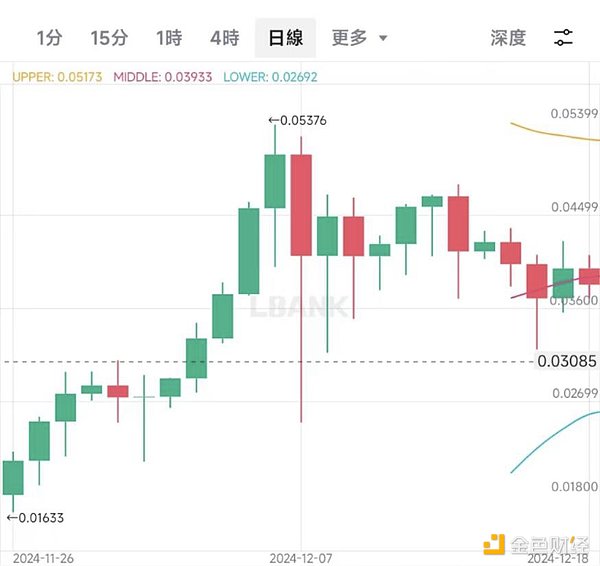注:原文來自deribit,在這篇文章中,作者Benjamin Simon對近期美國基礎設施法案的投票進行了反思,他認為,陷入僵局的基礎設施法案在許多方面標誌著crypto故事的新篇章,而致力於crypto長期成功的人,應該公開談論其中的哲學差異,而不是像我們經常做的那樣,將它們隱藏在晦澀的技術辯論之後。
此外,他還表示,我們最終需要做的不僅僅是理解這種基本衝突及其許多表現形式,我們需要的是一條中間道路。
本月早些時候,加密資產(crypto)(以有趣但有點可悲的方式)擾亂了美國政治。
參議院幾乎準備好就一項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法案進行投票,但最後一刻突然出現的一則條款,極大地擴大了對非託管crypto從業者(包括礦工和節點運營商)的報告要求。一小群活躍的加密原生DC監視者抓住了這一變化並迅速採取了行動。在一周的時間裡,crypto行業的領導者以及少數有權勢的CEO和企業家在遊說國會修改該法案。
儘管結果令人失望(最初的條款最終佔了上風),但這一過程是引人注目的。該修正案引發的騷動,最終迫使參議院將法案的最終投票推遲了數日,而其中還包括了一項新冠疫情救濟計劃。
無論如何,曾經是由技術未來主義者、無政府自由主義者以及正在康復的“撲克玩家”組成的邊緣隊伍,已經演變成了一個政治破碎球,Crypto把美國的立法系統拖入了一次緊急剎車。
Crypto不斷變化的精神
這一系列事件的重要性沒有被任何人忽視,《華爾街日報:“比特幣粉絲突然成為了一股政治力量”》、《華盛頓郵報:“crypto如何成為華盛頓的一股強大力量”》以及《政治:“華盛頓在基礎設施之爭中意識到了Crypto的影響”》等媒體報導,宣布了crypto行業翻開的新篇章。
然而,除了外界的關注以及媒體的喧囂之外,這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時刻還有更深層次的意義嗎?陷入僵局的基礎設施法案,似乎確實徹底改變了公眾對crypto及其力量的看法。但更根本的是,它揭示了crypto自身精神的演變。
自出現以來,一條共同的線索將crypto的不同部分和子群體聯繫在一起:一種差異性的身份,以及與先前存在的機構(無論是政治、經濟、金融還是文化)的自覺分離。比特幣誕生於2008 年金融危機之後,其最初是作為主權貨幣的替代品。以太坊背後的生動願景是(現在仍然是)一個擺脫矽谷科技巨頭封建統治的全球網絡。而DeFi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平行的、基本上自我封閉的金融體系。即使是最成功的文化藝術crypto項目(例如cryptopunks),也明顯地、自覺地打破常規。
當然,儘管分離主義思潮盛行,crypto行業已經看到了各種各樣的嘗試,它們試圖扭轉這一趨勢並容納傳統機構(還記得“是區塊鏈,而不是比特幣”嗎?)。但迄今為止,這些嘗試在很大程度上只是crypto故事的一個註腳——這個故事是由具有烏托邦、有時是革命野心的個人和運動所撰寫的。
陷入僵局的基礎設施法案在許多方面標誌著crypto故事的新篇章。在過去十年中,任何時候都不可能讓整個行業圍繞政治遊說活動展開活動——這不僅是因為crypto無能為力、不成熟和粗糙的,而且我認為,因為在十年的大部分時間裡,存在著強大的分離主義和脫離接觸的暗流。
這種最初的精神已經開始減弱,(非官方)領導層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證明了這一點。多年來,古怪的未來主義者、古怪的程序員以及不穩定的CEO 都在爭奪行業標準承載者的地位。而現在,包括美國參議員、對沖基金大亨以及沉默寡言的的科技億萬富翁們似乎在肩負著重任。
在我们的眼前,crypto正在经历一个显著的制度化,甚至是去激进主义的过程。
crypto站在十字路口
這種趨勢隱藏在每個人似乎都接受的“主流採用”的模糊概念背後。然而,它已經打開了,或者至少擴大了一個關鍵的意識形態裂痕。
當薩爾瓦多宣布將比特幣作為法定貨幣時,這一舉動贏得了crypto支持者的熱烈掌聲。但是當擬議的法律變更細節浮出水面時,這種熱情開始破裂。很多比特幣愛好者在得知薩爾瓦多政府將根據新法律要求企業主接受比特幣作為支付方式時發出了警報。在隨後的法律辯論中,出現了兩個陣營,其中一個角落里站著革命理想主義者,他們認為法律的強制性規定與比特幣的個人主權和選擇自由的核心理想背道而馳。而另一個角落是保守的實用主義者,他們承認任何州級政府採用比特幣,都必然涉及某種意識形態上的妥協。
這種割裂在crypto的其他地方也很明顯。 6月份,哈佛法學院區塊鍊和金融科技計劃(HLSBSI) 在Uniswap 的治理論壇上提交了一份提案,要求從協議財政庫中提取100萬UNI(價值2500萬美元)用於DeFi政治遊說活動。作為回應,Uniswap社區的很多成員表示了反對,他們認為這是一項誤導性的、自我挫敗的舉措。在dYdX 宣布將美國crypto用戶列入黑名單以進行追溯代幣空投後,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一些人對“去中心化”協議將屈服於法律限制感到憤怒,而另一些人則對遵守法規的舉措表示出了讚賞。
我在這裡描述的根本不是crypto陣營之間熟悉的爭吵,即俗稱的“有毒的最大主義”。相反,這是一種超越部落忠誠並觸及crypto最終目的核心的分裂:crypto應該努力創造一個不受傳統社會過時結構阻礙的嶄新系統,還是應該對主流政治、經濟和文化機構採取更為寬鬆的方針。
在crypto生命的大部分時間裡,它從未真正面臨過這種困境。在早期,甚至在2017-2018 年炒作週期的熱潮中,crypto基本上是一場邊緣運動。真正的信徒滿懷激情地堅持著它,懷疑論者認為這是幻想,而機會主義投機者來來往往。但現在,在經歷了一段令人矚目的增長後,crypto站在進一步製度化和重新致力於分離主義的烏托邦理想之間的十字路口。
這種困境不僅僅是理論上的。 crypto應該有一個有組織的政治遊說團體嗎?比特幣的支持者是否應該直接與中央政府合作以提高采用? DeFi協議是否應該將銀行和金融機構視為潛在的合作夥伴,而不是對手? crypto原生藝術家、策展人及文化場所是否應該與其主流同行合作?或者,crypto是否應該拒絕意識形態妥協,避免制度調整(不管是什麼),並回歸其革命根源?
如何追求變革?
這種困境對於crypto來說可能是新的(或者如果不是全新的,至少現在更加相關)。但從總體上和歷史上來說,它一點也不新穎。就這一點而言,我們也不應該對crypto現在面臨的困境感到驚訝。
幾個世紀以來,具有改變世界抱負的新興意識形態運動一直在應對同樣的挑戰。激進的政治團體在獲得權力後總是要努力保持他們的革命精神。宗教派別在其信徒是否應該在封閉的社區中追求與世隔絕的美德生活,或者他們是否應該與物質世界接觸以提升它(即使冒著稀釋宗教核心價值觀和實踐的風險)的問題上,分歧也很大。
關於crypto,這一困境似乎只是理想與實際之間的折衷。在這種框架下,爭論的雙方都認為,原則上,crypto應該盡可能地堅持烏托邦主義。接下來的問題是,在實踐中,為了行業的生存和繁榮,必須在多大程度上犧牲理想主義。這一框架隱含著一個假設,即與傳統結構和機構打交道沒有內在價值。一個真正獨立的烏托邦是可取的,卻是難以實現的,它需要對現實做出讓步。
然而,這種將困境定義為烏托邦主義與稍微實用的烏托邦主義的做法,忽視了第三種根本不同的方法。如果烏托邦的衝動不僅在實踐中行不通,而且在原則上實際也是不可取的怎麼辦?如果與傳統機構的接觸實際上值得稱讚,而不僅僅是對現實的讓步呢?總之,如果crypto不應該努力成為一場革命運動,而是一場改革運動呢?
這些問題肯定會讓普通的crypto支持者感到厭煩,但它們也有助於我們抓住問題的核心,因為最終手頭上的問題不僅關係到一個人對crypto的看法,而且關係到crypto渴望改變的世界。
例如,如果我們認為擁有主權貨幣的民族國家從根本上與自由不相容,或者金融機構和銀行已經腐爛到核心,那麼我們就不會有妥協的耐心。但如果我們的傳統政治、經濟和文化機構擁有一些智慧和價值(儘管它們常常讓我們失望),那麼它們當中有一些東西值得保留,crypto不應該成為孤立的系統。
中間道路
我想說的是,革命和改革的念頭都是有價值的。
在革命派的方法中,有著廣闊的視野、對現狀的不滿以及創造性的憤怒。這些對crypto的早期發展尤其有利,因為它們吸引了願意為邊緣運動投入大量精力和資源的個人。
而在改革派的觀點中,有一定的謙虛和感激,他們承認複雜的系統很難從頭開始構建。正如一位偉大的改革哲學家曾經說過的那樣,改革者的任務是在“守恆和修正兩個原則”之間取得微妙的平衡。特別是對於crypto改革者來說,這意味著努力使政治制度更加自由、金融制度更加公平、文化製度更加民主—— 但不是完全廢除制度。
毋庸置疑,這些變革與進步的決鬥哲學並不容易調和。我們這些致力於crypto長期成功的人應該認識到,這種衝突通常是crypto必須做出的許多價值負載權衡的核心。至少作為第一步,我們應該公開談論這些哲學差異,而不是像我們經常做的那樣,將它們隱藏在晦澀的技術辯論之後。
但我們最終需要做的不僅僅是理解這種基本衝突及其許多表現形式,我們需要的是一條中間道路。
事實上,縱觀歷史,找不到這條中間道路的運動都失敗了。在美國獨立戰爭之後的幾十年裡,聯邦主義者和反聯邦主義者圍繞戰後政府體系(聯邦條款)的可持續性展開了辯論。聯邦主義者主張建立一個更強大的治理結構,儘管他們意識到這樣做可能會部分損害自由的革命精神。而反聯邦主義者反對任何對國家建國理想的淡化。經過多年的辯論,最終於1787 年批准的《憲法》,對該國搖搖欲墜的政治制度進行了必要的改變,但它也在其強有力的《權利法案》中保留了革命的核心價值觀。在這個關鍵的早期階段,美國設法找到了一條中間道路。
而現在,crypto也必須這樣做,我們不能放棄核心革命精神,因為沒有它,crypto將失去其指導身份。但在crypto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盛行的根深蒂固的分離主義不再站得住腳。與那些讓我們失望的團體和機構直接接觸並不是軟弱的表現,而是力量的表現。
革命與改革、烏托邦與現實、分離與合作之間的這條中間道路,並不好走,它也不是很清晰,但這是必須要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