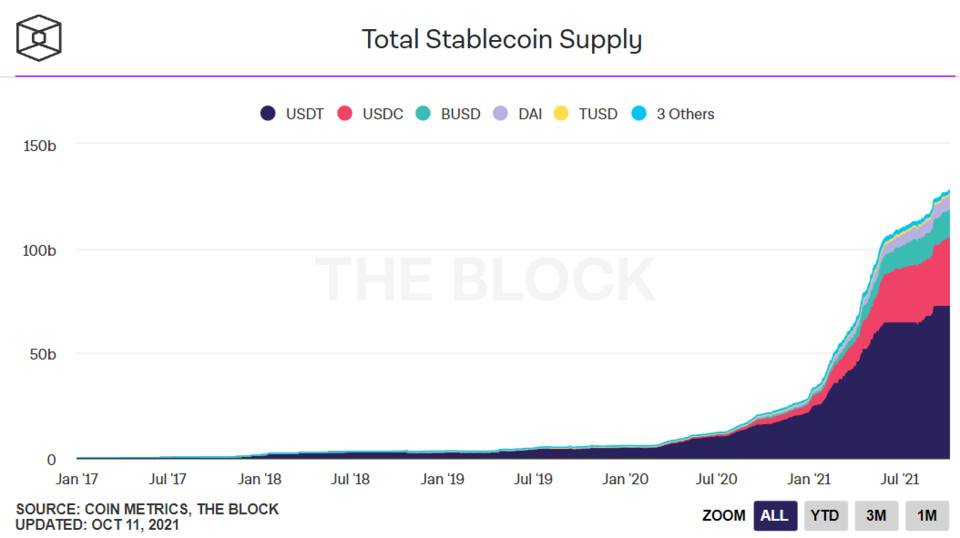中國開創了一種新的全球競爭方式,從而規避了困境。
本文來源於美國事務雜誌(American Affairs)作者Stephen Brent
譯者:劉斌中國(上海)自貿區研究院金融研究室主任
顛覆性創新的概念源於對公司創新的研究,但它也可以應用於國家。在這篇文章中,我將使用一些顛覆性創新的概念來分析美國和中國國家創新和增長的動態。美國本應是顛覆性創新的發源地,但哈佛商學院教授克萊頓·克里斯滕森(Clayton Christensen) 發現了限制公司對顛覆性技術投資的兩個困境。當發明新技術的公司無法將其商業化時,創新者的困境就會出現,因為這樣做會顛覆他們現有的業務。當公司因為高“門檻率”(要求的回報率)而拒絕進行顛覆性創新所需的風險投資時,就會出現資本家的困境。這些問題限制了美國經濟許多領域的顛覆性創新。科技行業是個例外,其中“新經濟”公司面臨著截然不同的市場動態。這些公司會採取贏著通吃的方式運營,其中成功所獲得的獎勵如此豐厚導致風險資本家會彼此競爭為充滿風險的創業企業提供資金。
中國開創了一種新的全球競爭方式,從而規避了這些困境。這種方法將廉價勞動力(至少在最初)與外國技術和高投資結合起來,以在目標行業發展競爭優勢。這一戰略讓中國橫掃了低工資和高價值的製造業領域,並實現了歷史上最快的增長。
但這一戰略也降低了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國家以製造業為主導的增長。部分原因是中國的做法在關鍵方面與美國相反:中國拒絕高門檻利率,轉而支持廉價資本和投資補貼,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其國家投資的總水平。事實上,無論有意與否,中國的戰略已經與美國的經濟偏好完美契合,美國是優先考慮股東的短期回報,而中國則優先考慮其工業和日益先進的技術的長期發展。
較高的最低資本回報率,低增長
大多數美國人都知道自大蕭條以來美國經濟增長和生產率增長一直緩慢,但許多人不知道放緩始於2000 年代初。問題不在於企業利潤下降——利潤上升了。問題在於,許多公司開始減少將其收入投資於可以提高生產能力的人力和物質資本。生產力增長在2004 年和大蕭條之後再次下降。
為什麼會這樣?有多種因果因素,但我將重點關注與顛覆性創新動態有關的一個驅動因素:新投資的最低資本回報率(hurdle rates)。
20世紀80年代,美國政府開始系統性地放鬆金融監管,美國公司在股東至上理論的影響下開始調整投資實踐。股東至上鼓勵公司專注於最大化股東回報。該理論認為,讓公司更多地關注股東利潤將導致更高的國家生產力和增長。
但事實並非如此。由參議員馬可·盧比奧(Marco Rubio) 領導的美國參議院強勁勞動力市場和國家發展項目最近進行的一項研究認為,過高的企業門檻率“減少了私人投資 [这已经导致]。 . . 經濟增長放緩、生產力增長停滯以及工人工資下降。 ”
理論上,企業最低資本回報率(投資要獲得批准必須滿足的要求回報率)應該與資本成本相關。如果投資資本回報率(ROIC) 超過加權平均資本成本(WACC),公司就應該進行投資。但這不是美國公司一直以來的運作方式。盧比奧報告引用的研究表明,“大多數大型上市公司使用的公司最低資本回報率比其’實際資本成本’高6.5% 至7.5%。”這意味著8% 的WACC 可能導致15% 的門檻回報率。在如此高的要求回報率下,公司將放棄許多本可以創造經濟價值的投資。正如報告所說,“如果一家公司使用資本成本而不是’實際’利率來做出投資決策,那麼. . .公司會投資不足,而且會出現未來的實際回報下降。
為什麼公司會設定明顯高於資本成本的最低資本回報率?報告認為,一個主要原因是金融部門的激勵結構。股東可以通過公司股票回購和其他金融工程方法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以很小的風險產生回報。因此,為了被認為是可行的,新投資在風險調整的基礎上必須比這些金融工程替代方案更具吸引力。而且由於對新創新的投資在較長的時間範圍內通常會帶來更大的風險,因此此類投資的預期回報門檻通常非常高,並且大大超過資本成本。
盧比奧的報告將美國當前的商業實踐與商業歷史學家阿爾弗雷德·錢德勒(Alfred Chandler) 所描述的美國早期“管理資本主義”模式的優勢進行了對比。在股東至上之前,福特、通用電氣和杜邦等公司並不關注短期回報,而是關注建立長期競爭能力,錢德勒認為這對持續生產力和利潤增長至關重要:
這些企業及其經營所在行業和國家的持續生產力、競爭力和盈利能力取決於不斷的再投資,以維持和改進特定產品的設施以及開發和維護特定產品的技術和管理技能。現代工業企業歷史的一個重要主題是,創造和保持這種能力是一個持續的、長期的過程——這個過程需要對企業健康穩健發展的決策者俱備長期、穩健的觀點。
克里斯滕森同樣認為,較高的最低資本回報率損害了長期生產力。他進一步區分了降低成本或裁員的“效率創新”與創造就業機會的“市場創造”或顛覆性創新。由於效率創新投資通常會很快獲得回報,因此它們通常可以通過較高的最低資本回報率測試。但由於創造市場或顛覆性創新通常需要花費數年時間才能獲得回報且失敗風險很高,因此它們往往不能獲得投資。因此,“公司主要投資於效率創新,這會減少工作崗位,而不是創造市場的創新,從而產生工作。”
克里斯滕森認為這是一個更大問題的一部分。當美國公司使用較高的最低資本回報率來限制投資時,他們將資本視為稀缺資產。但在經濟方面,資本並不稀缺;事實上,世界“充斥著資本”。全球金融資產的增長速度遠快於全球商品和服務的產出,借貸成本極低。這應該會產生更低的最低資本回報率和更高的投資。但美國公司不會那樣看待資本,這限制了資本主義履行其基本社會功能之一的能力——鼓勵熊彼特式的創造性破壞和國家經濟進步。正如克里斯滕森所說:
這就是資本家的困境。根據用於指導投資的工具,為長期繁榮做正確的事情對大多數投資者來說是錯誤的。在我們試圖最大化資本回報的過程中,我們降低了資本回報。資本家似乎對資本主義不感興趣——對支持創造市場的創新的發展不感興趣。
例外主義
如果資本家的困境是一個如此大的問題,矽谷是如何產生這麼多成功的公司(FAAMGs)的?資本家的困境約束不適用於他們嗎?事實上,答案是他們沒有。要了解原因,我們必須深入研究這些公司不同尋常的業務動態。
風險投資家彼得·泰爾(Peter Thiel) 提供了一些關於FAAMGs(Facebook,Amazon,Apple,Microsoft,Google)的最佳見解。彼得·泰爾認為,大多數矽谷公司都是從具有單一業務概念的初創公司開始的。許多初創企業在某一特定領域展開競爭,但通常只有一家出現並主導該領域。因此,在創業階段出現失敗的風險非常高。這使得打破常規的競爭變得激烈——初創企業和他們的風險投資支持者為了迅速擴大客戶數量,通常會接受巨額虧損。
他們這樣做是因為網絡效應的不尋常特徵——產品對每個用戶的價值隨著用戶數量的增加(通常呈指數增長)而增加。導致這種現象的因素在每種情況下都不同:微軟的商業軟件成為行業標準;谷歌有一個卓越的搜索引擎;Facebook 打造了首選的社交媒體產品。但在每種情況下,都有一家公司主導了市場並獲得了“贏家通吃”的回報。互聯網和軟件業務的低邊際擴張成本進一步強化了這些動態。一旦初始基礎設施到位,向網絡增加新用戶的成本以及擴展業務所需的時間相對較低,而製造業務則需要更多資金來擴展。
Thiel 很清楚,這些網絡效應企業往往獲得了巨大的壟斷力量。他認為這是一件好事。除了提供使風險投資具有吸引力的必要回報外,它還幫助公司快速開發新技術、廣泛傳播它們並投資於進一步改進。
而且,矽谷模式避免了創新者的困境。老牌公司通常很難投資顛覆性創新或將其商業化,因為這樣做會蠶食他們現有的業務線,需要新的業務方法,或者與現有的企業文化發生衝突。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克里斯滕森建議公司將顛覆性創新放在不同的部門或創辦新公司。矽谷初創企業以獨立企業的身份起步,希望打破現狀,從而完全避免了這個問題。
其次,初創企業和他們的風險投資支持機構確實不得不擔心回報率、預期的投資回收期和失敗的風險,但由於贏家通吃的影響,這些問題更容易得到滿足。失敗的風險極高,但獲勝的回報——壟斷回報的前景——是如此之大,以至於越來越多的資金流向風險投資者以追逐這些機會。
FAAMGs的經濟主導地位表明,美國在未來的經濟和技術競爭中處於有利地位,美國在引領創新方面的良好記錄和我們大學的實力也是如此。這些都是真正的優勢。但美國也有一些弱點。
首先,FAAMGs的技術創新並沒有導緻美國主流企業的廣泛變革。正如泰爾所觀察到的,我們已經看到了比特世界的創新,但沒有看到原子世界的創新。很難將數字技術集成到非IT 業務中。例如,決定哪些企業流程最能從人工智能中受益,需要了解業務和技術。此外,正如哈佛商學院教授Gary Pisano 和Willy Shih 所指出的那樣,由於先進的製造業和技能組合已經遷離美國,這種創新所涉及的挑戰變得更加困難。
二是基礎研究公共經費下降。美國領導IT 革命的關鍵之一是美國政府在1950 年代和60 年代對基礎研究和技術教育進行了大量投資。這項投資是出於國家安全的考慮,但它產生了許多導致矽谷崛起的基礎技術。正如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喬納森·格魯伯(Jonathan Gruber) 和西蒙·約翰遜(Simon Johnson) 所言,私營公司不會在基礎研究上投入足夠的資金,以及基礎研究的突破嚴重依賴公共資金的原因是有經濟理由的。美國仍然是公共研究的主要資助者,但與蘇聯人造衛星事件後佔GDP 的2.0%峰值相比,該資金大幅下降。今天,佔GDP 的0.7%,而且還在下降。
中國的顛覆性創新
當中國在70 年代後期開始改革和發展時,它藉鑑了東亞國家的先例,對其進行了修改以滿足其需求,並開創了一種新的外國投資方式。
在某些領域,中國毛主席以後的領導人追隨了東亞前輩的腳步。與日本、韓國、台灣和其他國家一樣,中國擁護國家行動主義、產業政策和重商主義。但中國也修改了東亞模式。首先,它更加依賴廉價勞動力作為其競爭優勢的主要來源。其次,它進一步推進了東亞高儲蓄和高投資的做法。大多數“亞洲四小龍”的投資水平在巔峰時期在GDP 的25-35% 之間,但中國的投資達到了GDP 的35-45%,令人難以置信。
這些漸進式創新可能讓中國實現了相當強勁的追趕式增長。但中國高速增長的關鍵——使其處於不同聯盟的主要因素——是其對待外國技術的獨特方法。在鄧小平推動經濟增長的一開始,中國領導人就做出了歡迎外國投資的關鍵決定。這與日本和韓國所採取的路徑(均阻止外國投資)大相徑庭。
令人驚訝的是,中國領導人能夠在沒有經過大量辯論的情況下就這一政策達成一致。為什麼?一個原因是它不是對意識形態的直接挑戰。關於國內經濟改革的決定是有爭議的,但外國投資被更多地看待。中國長期以來一直對獲取外國技術感興趣(可以追溯到蘇聯時期),而外國投資是實現這一目標的一種方式。中國領導人也仍然被毛澤東的大躍進思想所吸引。他們認為外國投資有助於實現這一目標——正如他們所採用的標籤所暗示的那樣:“外國大躍進”(有時翻譯為“西方大躍進”)。
新模式開始迅速產生效益。中國開放邊境後不久,來自香港和亞洲其他地方的投資者就開始在深圳開展製造業務,這使得該地區的出口增長迅速(每年翻一番)。隨著區域投資在沿海地區的擴大,收益增加,推動了中國製造業出口的許多增長。很難說如果沒有外國投資,中國會增長多快。其對農業和鄉鎮企業的改革會帶來一些增長,但外援出口部門是關鍵。它幫助中國加快了將工人從農場轉移到工廠的速度,極大地提高了生產力。
入世後中國的增長
中國的增長在1980 年代和90 年代強勁,但中國在GDP 總量中的絕大部分增長是自2001 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實現的。美國決策者非常支持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美國的支持幾乎沒有附加條件。由於加入世貿組織將要求中國減少關稅壁壘,許多人聲稱這會產生有利於美國的片面收益。然而,中國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看待世貿組織:它將利用世貿組織良好管理的印記,更積極地推動製成品出口,並利用外國公司的利益來幫助它實現這一目標。
中國按要求降低了關稅,但在早些年,它取代了一種低估的貨幣,有效地懲罰了進口並補貼了出口。它還利用其可用所有工具來補貼投資和出口,最大限度地獲取外國技術,並主導低工資製造業。
在這個過程中,美國和其他西方公司渴望在中國投資,這極大地幫助了中國。西方投資在1990 年代開始增加,但在2001 年之後開始加速。這些公司有兩個動機:進入中國不斷擴大的國內市場的底層,並將中國作為其出口價值鏈中勞動密集型階段的生產基地。
一方面,技術的根本性變革促進了第二個功能,另一方面,以股東為導向的公司管理日益盛行。信息技術和通信的新發展使西方公司能夠在不同國家定位其價值鏈的不同階段。結果,公司更容易將生產的勞動密集型階段離岸,他們熱情地這樣做。美國公司特別熱衷於離岸,因為它幫助他們應對來自股東日益增加的壓力,要求降低資本密集度和增加回報。
在英國經濟學家理查德·鮑德溫(Richard Baldwin) 的說法中,西方的離岸業務本可以流向許多低收入國家。但在實踐中,絕大部分都流向了中國,因為中國有製造基地,是低成本生產國,外國投資者很容易建立有利的合作夥伴關係。離岸外包要求西方公司將技術輸送到中國,以使先進的生產流程發揮作用。這意味著中國主導了其廉價勞動力和西方技術的結合,從而將其經濟推向了另一個層次。 2001 年至2007 年,外國技術不僅幫助中國將其出口以美元計價的價值增加了五倍,而且還提高了這些出口的技術水平。這幫助中國實現了生產力的快速提升和產業的快速升級。
全國戰略
中國還使用合資要求、強制技術轉讓、知識產權、龐大的海外獎學金計劃和其他方法來促進技術和製造業從西方國家轉移到自己的市場。
想要在中國投資或銷售的西方公司往往不得不遵守合資要求並接受強制技術轉讓。公司通常願意做出這些重大的技術讓步以換取短期利益(再次滿足股東)。它已經向西方大學輸送了數以千計的技術類學生,中國成為技術合作、共享研究和跨越國界的研究實驗室的大力倡導者,這使其能夠接觸西方知識。
此外,中國非常善於將外國技術應用於本土需求。商業分析師Dan Breznitz 和Michael Murphee 表示,中國公司在很大程度上並不試圖在技術前沿與西方公司競爭。相反,他們專注於“落後一步”的產品。他們專注於流程改進,使他們在跨國生產中成為更有效率的合作夥伴,或者使他們能夠生產更適合中國和其他新興市場國家市場的低成本產品。中國公司通過創造以50% 的成本提供80% 價值的本地產品而取得了巨大成功。
最後,中國對公共和私人投資採取了截然不同的方法。首先,它將研究和技術教育的公共投資視為國家經濟和安全戰略的工具。它一直在穩步增加這項投資,並將大部分投資重點放在關鍵技術上,例如量子計算、機器人和基因工程。
其次,中國完全拒絕美國較高的最低資本回報率模式。在中國看來,資本的目的不是為了確保個人投資的高回報率,也不是為了個人股東的價值最大化,而是為了實現總投資的最大化——因為這樣可以最大化產業進步的步伐。為了最大化投資總量,資本應該便宜或免費,甚至由政府提供。中國省級和地方政府定期向受青睞的投資者提供免費土地、企業倒閉時可能無需償還的低成本貸款以及政府採購方面的優惠待遇。他們正在積極補貼企業投資。
如果中國認為該行業對未來增長很重要,那麼它也願意承擔啟動一個新行業的成本。例如,政府對電動汽車的發展給予了廣泛的補貼,包括在市場需求之前公共資助一個充電站網絡,中國版的“你建了它就會來”。
這些做法與西方規範大相徑庭,但在促進工業快速發展方面非常有效。在外國技術的推動下,生產力的強勁增長和極高的投資相結合,形成了強大的組合拳。
結果是世界一流的。 2001-2013年,流入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FDI)增長了300%,中國在全球製造業中的份額增長了400%,中國出口增長了500%。 2001年至2016年,中國在全球製造業增加值中的比重從6%提高到26%,超過美國和歐盟成為全球最大的商品製造國。根據投資銀行家斯圖爾特帕特森的說法,“在本世紀的頭十年,又有2.05 億人從農村遷移到城市地區。在接下來的15 年裡,工資將增長12 倍。”
專家認為,外國投資對中國的高速增長負有很大一部分責任。例如,商業分析師邁克爾·恩賴特(Michael Enright) 估計,2013年外國投資者和外商投資企業佔中國GDP 的33%,佔其就業的27%。新模式結合了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和對強大製造業基礎的投資意願以及西方公司的尖端技術、技能和營銷。這一戰略確實對中國造成了輕微的影響——讓外國公司在中國銷售會讓本土公司更難參與競爭。但中國在合資企業和強制技術轉讓中獲得了補償性收益,這些收益要高得多。總體而言,該戰略對中國來說幾乎是純粹的收益。
其他國家已買單
對世界其他地方就不能這樣說了。如果中國把西方國家的技術和製造轉移到自己那裡,那就是西方國家蒙受了損失。這些損失有多大?經濟學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新古典主義傳統中的許多人認為西方的成本並沒有那麼大,而其他人則說成本相當高。後一組包括理查德鮑德溫,他談到離岸外包:
結果是發達經濟體發生了相當突然和大規模的去工業化。 . . . 發達經濟體的工業化花費了一個世紀的時間。去工業化和製造業向新興國家的轉移只用了二十年。 . . . [西方] 工人不再享有獲得本國公司開發的專有技術的特權。發達經濟體工人過去對發達經濟體技術的壟斷被打破了。
投資銀行家斯圖爾特帕特森同意。他認為,“從2001 年開始與中國的經濟接觸導致發達國家工人的實際收入能力迅速而急劇地惡化。自維多利亞時代以來,發達國家的收入中位數從未停滯這麼長時間。”
這些對西方製造業的負面影響現在越來越多地被討論,但對發展中國家工業進步的負面影響卻很少受到關注。中國喜歡把自己描繪成發展中國家的冠軍,但經濟現實是,它在低工資製成品出口和西方離岸外包方面的主導地位如此之大,以至於其他發展中國家很難或不可能發展自己的產業。 “中國價格”如此之低,以至於其他生產商無法與之競爭。如果說製成品出口是窮國想要進步的“增長扶梯”,那麼中國已經將其他發展中國家擠在扶梯上。他們被迫依賴大宗商品出口,通常是出口到中國,這可能會在一段時間內促進他們的增長。
新的遊戲
這些影響並不完全是中國造成的。中國在鼓勵投資和獲取外國技術方面做出了明智的選擇,但當其政策受到外部發展的支持時,其戰略的全部力量才出現:價值鏈的轉變,西方決定以很少的條件接納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及受到對股東價值的狹隘關注,西方公司積極追求離岸外包。
中美未來走向何方?我將提供三個預測。
首先,中國的高速增長可能已經結束。自大衰退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已經放緩,而且由於老齡化、工資上漲和高企的企業債務,中國的增長可能會進一步下降。然而,中國領導人也知道這一點,這進一步激勵了他們實現本土技術主導地位的努力,正如“中國製造2025”戰略所體現的那樣,該戰略要求在關鍵先進行業培養全球冠軍。
其次,中國將繼續受益於來自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技術流動。美國公司將繼續希望在中國銷售產品並維持生產。由於“中國製造2025”戰略和其他緊張局勢對關鍵技術構成的威脅,一些政界人士正在重新考慮這些參與,但企業領導人和股東對大規模外流沒有興趣。中國也將繼續受益於西方機構的開放性。
第三,中國公司對包括科技公司在內的西方公司構成的挑戰可能會增加。預計中國企業將進一步推進以50% 的成本生產價值80% 的商品的戰略,這將使它們處於優勢地位,以服務預計將領先的新興市場國家不斷擴大的客戶群,他們將引領未來的全球需求。中國公司也很可能成為全球核心基礎設施技術(例如5g 組件)的主要供應商,這將推動它們的公司進一步向價值鏈上游發展。與此同時,除非進行重大改革以改變對美國公司和金融機構的激勵(以及增加政府研究),否則美國
正如克里斯滕森所說,來自低成本端的挑戰者可能是強大的競爭對手,而在位者往往看不到這些新威脅的到來。
本文最初發表於美國事務第三卷,第4 期(2019 年冬季):29-42。
展開全文打開碳鏈價值APP 查看更多精彩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