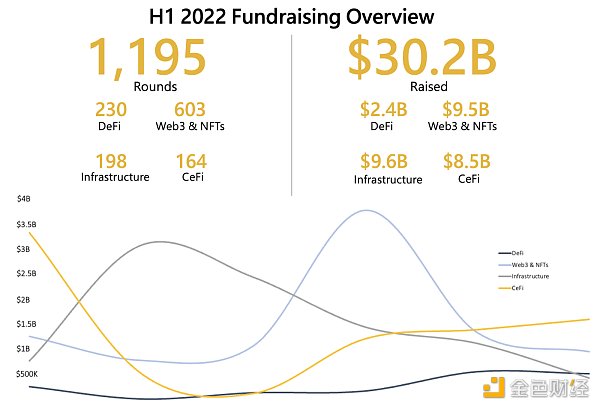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朱英子北京報導 5月5日,北京法院審判信息網披露了一份刑事訴訟案件判決文書,案涉價值5000萬元的虛擬貨幣被盜,包括泰達幣、以太幣、比特幣。
最終,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下稱“朝陽法院”)否定了辯護人提出的構成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的辯護意見,支持了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檢察院(下稱“朝陽檢察院”)的指控,裁定被告犯盜竊罪,判處有期徒刑12年,罰金20萬元,剝奪政治權利2年。
值得關注的是,在司法實踐中,各地法院對於盜竊比特幣的行為認定上是有分歧的。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合夥人、中國銀行法學研究會理事肖颯2021年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竊取比特幣類案件目前大量存在,從刑事判決情況看,竊取比特幣的刑法定性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是將比特幣認定為財產,符合刑法盜竊罪構成要件的,構成盜竊罪;另一種是認為比特幣是一種數據,竊取比特幣構成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罪。該案中的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則與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罪類似。
盜竊者入侵平台系統
據裁判文書顯示,2019年年初,而立之年的凌月生(化名)在廣東省雲浮市雲城區某暫住地處於無業狀態,小學文化的他想著通過手機“薅羊毛”,便在百度上搜索如何破解網絡請求包和入侵計算機信息系統的教學。
之後,凌月生髮現了一個篡改網絡請求包內數據的辦法,還將這個辦法告訴了同住的老鄉凌士山(化名),凌士山也是小學文化。從那時起,兩人就一直嘗試入侵北京某信息技術公司服務維護的某數字資產交易平台系統。
“我用鼠標抓頁面上的數據,點來點去,最後就找到漏洞了。”凌士山供述稱。 2020年10月份,凌士山在使用凌月生賬號時發現了該系統的劃轉漏洞,通過一個抓包軟件在該平台上抓取數據,然後手動將抓取的數據開頭添加“-”號發送至平台,就可以看到自己在平台的錢包賬戶內的虛擬貨幣增加。
據北京某信息技術公司報案材料、系統後台日誌顯示,2019年10月16日,凌月生在上述平台註冊賬號嘗試攻擊其維護的系統,持續至2020年10月15日凌晨4點成功侵入該系統。後註冊凌士山實名賬戶成功侵入該系統,又陸續註冊了17個實名賬戶通過這兩人的設備輪流登陸對系統漏洞進行攻擊,成功後提現。
僅16日凌晨2點到5點15分期間,兩人總計盜取泰達幣62萬個,以太幣12687.9956個、比特幣149.99627927個。凌月生將盜取的虛擬幣的私鑰放在一部金色蘋果手機裡面,存在其堂妹暫住地保險櫃內,此外兩人總計變現了約200萬元人民幣,用於購買寶馬車等支出。
據上述信息技術公司法定代表人田某證言,16日早上9點,公司平台維護人員才發現其所服務的平台發生異常大額提現情況,當時泰達幣的售價大概每個6.7元人民幣,以太坊售價大概每個2500元人民幣,比特幣售價大概每個7.9萬元人民幣。 “我公司受XX Global XX Ltd.委託對某數字資產交易平台進行系統研發維護和技術諮詢服務,依據我公司與該公司簽訂的技術服務合同,此次系統入侵事件,我公司按照協議需賠付對方公司人民幣5025.97萬元。”
發現該漏洞後,信息技術公司對該漏洞進行了檢修,之後田某向公安機關報案,通過公司日誌,鎖定了凌月生和凌士山。田某還稱,為修復系統漏洞,公司還聘請了第三方對系統進行安全修復,花費20萬元。
2020年10月21日,公安機關將凌月生和凌士山抓獲歸案,次日被刑事拘留,於2020年12月8日被逮捕,現羈押於北京市朝陽區看守所。
數據還是財產?量刑何解?
2021年5月6日,朝陽檢察院向朝陽法院提起公訴,認為被告人凌月生、凌士山的行為觸犯了刑法第三百六十四條的規定,應當以盜竊罪追究其刑事責任,提請法院依法判處。
但是,被告人凌月生及其辯護人對於指控的罪名持異議。辯護人認為,涉案虛擬貨幣不屬於財產,涉案交易平台系境外違規平台,不應得到法律保護,且指控犯罪數額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故本案被告人的行為不構成盜竊罪,而應以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定罪處罰。
對於上述辯護意見,朝陽法院表示,根據央行等部委發布的《關於防範比特幣風險的通知》《關於防范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等規定,案涉比特幣、泰達幣、以太坊等虛擬貨幣不具有法償性和強制性等貨幣屬性,不屬於貨幣。
“但上述規定未對虛擬貨幣作為虛擬商品的財產屬性予以否定,我國法律、行政法規亦並未禁止比特幣的持有和轉讓。”朝陽法院在認為部分如此表述。
法院還指出,《關於防範比特幣風險的通知》中提到,“從性質上看,比特幣是一種特定的虛擬商品”,因此,虛擬貨幣具有財產屬性,為財產性利益,屬於盜竊罪所保護的法益。
朝陽法院認為,被告人在非法佔有目的的支配下,實施了侵入並攻擊計算機信息系統的手段行為和盜取虛擬貨幣後進行變賣獲利的結果行為,符合盜竊罪的構成要件,應當以盜竊罪定罪處罰,而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只涉及對其手段行為的評價,並未對犯罪行為進行完整評價,故不採納辯護人的辯護意見。
其次,對於辯護人提到的“指控犯罪數額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這一意見。法院認為,被告人盜竊虛擬貨幣的總體價值缺乏權威、中立的評估機構進行認定,故本案不以5000餘萬的平台交易價值來認定二人的犯罪數額。
法院進一步指出,但被告人盜竊虛擬貨幣後變賣獲利200餘萬元是客觀和現實的,基於事實和法律,本案以銷贓數額作為對被告定罪量刑的基礎。
北京德恒律師事務所律師劉揚對此分析稱,法院最終以被告變現金額認定為盜竊的犯罪所得,以此來量刑是比較妥當的,但對於一些沒有變現的盜幣案,或者說獲利後又經過反復交易的,在最初數額無法認定的情況下,建議以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罪來追究刑事責任。
此外,朝陽法院認為,涉案平台是否屬於違規平台,與該平台上的虛擬貨幣是否屬於法律所保護的財產,屬於兩個範疇的問題。且對於涉案平台屬於違規應關停平台的意見,辯方未提供確實充分的證據予以證明。 “但即便是非法佔有的財產,在經過法定程序恢復應有狀態之前,該佔有亦是盜竊罪所保護的法益。故涉案平台的法律屬性,不影響對被告人行為的定型。”裁判書中如此載明。
最終,法院分別判決被告凌月生和凌士山犯盜竊罪,判處有期徒刑12年,罰金20萬元,剝奪政治權利2年,繼續追繳違法所得。
結合近期北京市仲裁委的一次涉比特幣民事裁決以及近期的涉幣判例可以發現,北京地區的法院普遍支持“比特幣等虛擬貨幣屬於虛擬財產,受到法律的保護”這一審判思路,但裁判規則亦有所變化。
裁判規則的變化
“關於盜竊虛擬數字貨幣的案件,北京地區的裁判規則在各個時間段是不太相同的,大致可分為三大階段。”劉揚向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介紹道。
第一階段是2017年9月4日之前,相關案件多以盜竊罪定罪處罰。例如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2015)東刑初字第1252號判決書顯示,法院認為,被告人以非法佔有為目的,秘密竊取他人財物,數額較大,其行為侵犯了公民的財產權利,已構成盜竊罪,依法應予刑罰處罰。
第二階段是2017年9月4日至2021年期間,以七部委聯合發布《關於防范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開始。
劉揚提到,上述公告中明確“不得為代幣或’虛擬貨幣’提供定價、信息中介等服務”,而盜竊罪是財產類犯罪,通常需要對被盜物品進行價格鑑定,價格鑑定部門囿於該公告的影響,無法出具價格鑑定報告,盜幣案件的處理一時間成為全國司法機關的一大難題,但這類行為又是侵犯刑法法益的行為必須要打擊,因此便從虛擬貨幣的數據屬性切入,認定為“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罪”或“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
2018年7月6日,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檢察院以京海檢科技刑訴〔2018〕70號起訴書指控被告人犯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該被告在擔任比特大陸運維開發工程師期間,轉移了公司100個比特幣至自己的電子錢包裡。最終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支持了指控罪名成立。
劉揚稱,該案件為全國司法機關在上述公告發布後如何打擊盜幣案件開拓了思路,也是全國第一起被以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追究刑事責任的盜幣案件。
第三階段是2021年之後,兩種罪名的認定均有“支持者”,各地審判亦現分歧。 2021年以來,隨著比特幣的價格一路走高,更多人加入到炒幣大軍中,該領域違法行為日漸高發。
“在這種情況下,我個人認為,司法機關的工作人員內心也悄然發生了變化,比如以前,內心認為數字貨幣一文不值,但現在,案件的具體承辦人員內心都知道虛擬數字貨幣就是真金白銀。”劉揚向記者提到,部分司法人員會認為以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量刑畸輕,罪責刑不相適應。
同時,司法機關也加強了對虛擬數字貨幣刑事犯罪的研究。
2021年5月份,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檢察院第二檢察部一級檢察官李慧在《中國檢察官》雜誌撰文稱,“在涉案金額特別巨大的前提下,認定計算機相關犯罪將導致量刑畸輕,是否具有懲治意義也需要進一步考究。而對於涉及侵財類犯罪的刑法理論,也尚需要在虛擬貨幣的背景下進一步加以變通和擴充。”
反對者亦有之。在2021年7月份召開的第二屆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刑事實務論壇上,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刑事處處長喻海松提出,虛擬財產無疑具有財產屬性,但是否屬於財物,前置法尚未明確。在前置法律依據不明的情況下,具有財產屬性並不必然意味成為刑法上的財物,對相關行為不一定要適用財產犯罪。
“關於虛擬財產的法律屬性,民法界爭議很大。刑法是其他部門法的保障法,在前置法尚未明確的情況下,刑法衝到最前面不一定是最好的選擇,應當堅守刑法的二次法屬性,盡量秉持謙抑立場。”喻海松如此認為。
“導致這一結果出現的根本原因在於,比特幣在我國的法律地位並不明確,監管政策曖昧。”晟典律師事務所律師鐘海偉在2021年6月份發表的文章中指出,將“盜竊” 比特幣的行為定性為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的進路更像是迴避討論比特幣財產屬性問題的權宜之計,而直接將“盜竊”比特幣行為定性為盜竊罪的做法,則不可避免需要面對來自於刑事政策角度與可行性的質疑,兩種進路均難言妥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