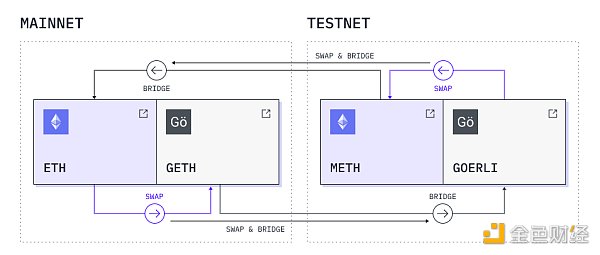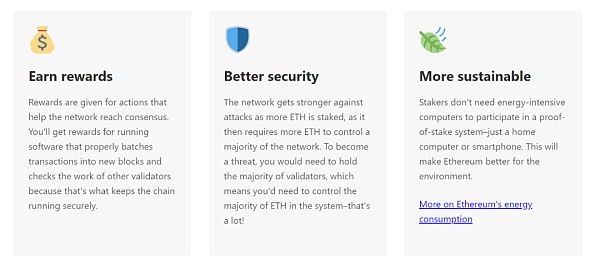從Web1.0到Web3.0,我們經歷了互聯網數據內容從可讀到可寫,再到可持有的整個過程,整個互聯網的生態和格局也在不斷演進中呈現出更加多樣的可能性,用戶漸漸成為了網絡數據內容最主要的來源之一,換言之,傳統互聯網大廠正在從內容的創造者、控制者轉變為網絡技術服務的提供者、數據聚合者和內容展示者。
無論是從Web2傳統大廠來看,還是從Web3目前最主要的用例NFT數字藏品來看,PGC平台都正在漸漸向UGC平台轉化和過渡,並且,由於UGC平台的流量變現功能和海量的新奇內容,使得以UGC內容為主的平台的活躍度明顯高於傳統以PGC內容為主的平台。這一趨勢某種程度上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可靠的預測:UGC平台才是未來。
但是,UGC平台在為用戶提供更多消費產品、更多變現渠道的同時,對於用戶上傳的內容卻難以做到有效審查,諸多侵權作品、抄襲作品充斥平台,這不僅侵犯了原作品權利人的合法權益,也為平台增加了大量的侵權風險。颯姐團隊今天就與大家深入聊一聊,我國UGC平檯面臨的困境,並從中尋找出路。
一、PGC到UGC,一場用戶權利的革命
UGC是互聯網術語,全稱為User Generated Content(也被稱為UCC,即User-created Content),可以理解為“用戶生成內容”或“用戶原創內容”。這一概念最早起源於互聯網領域,即用戶將自己原創的內容通過互聯網平台進行展示或者提供給其他用戶。 UGC是Web2.0區別於Web1.0最本質的特徵,使得用戶從互聯網的消費者漸漸變為了互聯網的參與者和生產者。與之相對的,則是PGC,全稱為Professional Generated Content,從字面意義理解,即專業生產內容。傳統的廣播電視行業就是典型的PGC模式,用戶打開電視只能被動接受電視台輸出的內容,不僅無法參與電視內容的創造,甚至無法選擇自己想看的內容。
從PGC到UGC實際上是一個權利逐漸下放於用戶的過程,或者說,這是一場用戶權利的革命,但與Web1到Web2由互聯網巨頭自上而下的變革不同,Web3革命是由用戶發起的,自下而上的“奪權”。隨著高速移動網絡、雲計算、智能終端設備的發展,用戶對互聯網內容漸漸擁有了選擇權和創造權,而Web3革命的核心要義,就是讓用戶進一步擁有對互聯網內容的控制權。當然,該控制權僅及於用戶自身創造的或享有某些特定權利的內容,Web3 Builder們將這一願景寄託於區塊鏈技術來實現。
二、 中國UGC平台們面臨的侵權風險
UGC平台千千萬,從大廠到小廠,從短視頻到音樂圖片,都面臨著一個嚴肅的問題:侵權。某著名圖片版權平台還專門開發出一套全網侵權檢測系統,對各大UGC平台進行監控,一旦發現平台上存在用戶上傳的侵權作品,立刻就會重拳出擊。甚至有一些品行惡劣的平台還會採用“釣魚執法”的方式,故意將版權內容散播到各大平台,引誘他人侵權。正是由於此等“版權巨魔”的存在,UGC平台們往往面臨著很高的侵權風險。
對於用戶上傳內容侵權平台是否承擔侵權責任?承擔多大的侵權責任?在以往的司法實踐中普遍使用兩個原則進行判斷和考察:避風港原則和紅旗原則。
所謂“避風港原則”,指的是在發生網絡侵權事件時,網絡服務提供者在接到權利人的合法通知後,及時依法採取必要措施的,無需承擔侵權責任(又稱“通知-刪除”原則)。 “紅旗原則”指的是網絡服務提供者對顯而易見的侵權行為,選擇視而不見的,應該承擔法律責任。 2020年公佈的《民法典》中,吸收了二者,同時又在整合已出台法律規定和司法實踐經驗的基礎上,作出了一定的突破,構建起了一個更具可操作性的網絡侵權責任規範體系。而對於UGC平台來說,其審核義務卻加重了。
目前在司法實踐中,UGC平台往往因為“沒有盡到較高注意義務”而被法院判決承擔侵權責任,而該“較高注意義務”的來源,則是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侵害信息網絡傳播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第十一條:網絡服務提供者從網絡用戶提供的作品、表演、錄音錄像製品中直接獲得經濟利益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其對該網絡用戶侵害信息網絡傳播權的行為負有較高的注意義務。
那麼,何為“直接獲得經濟利益”?該條司法解釋第二款明確:網絡服務提供者針對特定作品、表演、錄音錄像製品投放廣告獲取收益,或者獲取與其傳播的作品、表演、錄音錄像製品存在其他特定聯繫的經濟利益,應當認定為前款規定的直接獲得經濟利益。網絡服務提供者因提供網絡服務而收取一般性廣告費、服務費等,不屬於本款規定的情形。
三、應如何理解《規定》?司法實踐存在爭議
按照《規定》第十一條,判斷平台是否需要承擔較高注意義務,取決於其是否從用戶上傳作品中“直接獲得經濟利益”。但颯姐團隊認為,《規定》第十一條存在模糊和矛盾之處,在司法實踐中存在爭議。
《規定》要求的“存在特定聯繫的經濟利益”應當指的是在侵權行為發生時,可以確定的、與作品相關的、能夠由網絡服務提供者獲得的經濟利益。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如果在侵權行為發生時,該經濟利益尚不能確定是否會由平台方獲得。
用NFT數字藏品UGC平台舉例,誰都不能保證用戶上傳的NFT一定能被賣出去,那麼如果該NFT無法賣出平台當然也無法獲取任何經濟利益。如果一直賣不出去,此時根據司法解釋第一條規定,無論如何解釋,都無法認為“網絡服務提供者從網絡用戶提供的作品、表演、錄音錄像製品中直接獲得經濟利益”。故而根據規定,此時網絡服務提供者便不會承擔較高的注意義務。
這樣的後果是,平台是否承擔較高的注意義務完全取決於審查時尚不能確定的一種可能性事件,取決於審查後不知多久才能實現的結果,甚至於完全可能存在被侵權人促使該事項發生從而向平台主張責任的情況,這無疑會滋生極大的道德風險。
颯姐團隊認為,如果司法解釋制定者想要網絡服務提供者針對不確定的經濟利益也需要承擔更高的注意義務,完全可以將司法解釋制定為“網絡服務提供者從網絡用戶提供的作品、表演、錄音錄像製品中直接獲得經濟利益或者俱有直接獲得經濟利益的可能性的”或是“網絡服務提供者從網絡用戶提供的作品、表演、錄音錄像製品中直接或間接獲得經濟利益的”。但最高法最終採取的方案是確定為“網絡服務提供者從網絡用戶提供的作品、表演、錄音錄像製品中直接獲得經濟利益的”,可見,只有在審查時已經確定網絡服務提供者能夠從中獲益的情況下,才能認定為直接獲得經濟利益,從而要求平台在審核時就盡到“較高注意義務”。
寫在最後
當然,除此之外,我國法律並未對“較高注意義務”作出明確規定,從司法實踐來看,即使平台已經使用AI+人工雙審核機制,但由於平台每天的上傳量較為巨大,依然難以防止出現漏網之魚。誠然,漏網之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平台審核機制的不完善,但試問當前又是否存在盡善盡美的審核?
颯姐團隊認為,較高注意義務應當有一個合理邊界,其判斷標準既要考慮到本行業的商業習慣,又要考慮到行業的平均審核能力,制定出切實可行的指引。另外,在司法實踐中,法院應當對“釣魚執法”、“撒釘子”式侵權訴訟,進行合法、合理的區別對待,切勿讓法律成為不當牟利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