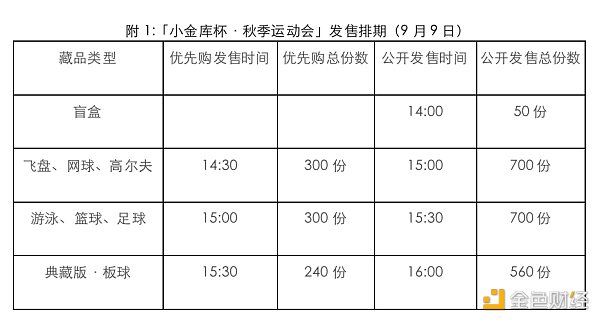原文作者:Vitalik Buterin 原文標題:Why I Built Zuzalu 原文來源:palladiummag 編譯:Joey Zhong
這篇文章是Vitalik 從第一人稱的視角討論了一個名為Zuzalu 的實驗性社區,該社區旨在將線上文化和部落轉化為物理場所,並探討了其背後的思想和實踐。作者強調了Zuzalu 的獨特之處,將其描述為一個跨國虛擬社區,它與加密貨幣領域有關,同時也擁有自己的目標和文化。 Zuzalu 的實驗包括建立一個可容納200 人的迷你城市,持續兩個月的時間。這個實驗的目標是融合不同文化,創造一種獨特的社區感。文章提到了實驗的一些成功之處,包括技術和社交的進展,以及社區的國際化。然而,文章也提出了一些問題和挑戰,包括Zuzalu 的規模和目標,以及如何在長期內保持其特殊性和吸引力。作者認為,Zuzalu 可能會發展成一個具有大學、修道院和數位遊牧中心等特點的結構,但仍需要不斷探索和發展。總的來說,這篇文章討論了一個有趣的實驗,探討了線上和實體社群的融合,以及如何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塑造和發展文化和社交聯繫。
譯者註:Zuzalu 並沒有正式的官方譯法,拼音直譯為“祖扎魯”, 譯者詢問過Vitalik,Zuzalu 是他創造出來的一個有趣詞彙,並沒有獨特意思,但是在Zuzalu 中文社區,被廣泛使用的非正式暱稱是“豬豬樓”。
我們傾向於認為實體場所以及這些場所所帶來的活動和文化是一成不變的。作為個人,您可能可以選擇搬到一個特定的地方:前往舊金山,欣賞其開放和接受的文化或人工智慧開發場景,前往柏林,欣賞開源黑客文化,或前往亞洲,成為新的世界的一部分和正在崛起的世界。
同時,我們將所有這些特徵視為給定的,作為人類世界的外生和固定部分——你必須在存在權衡中做出選擇。但如果情況可能有所不同呢?如果在網路上形成的具有自己的目標和價值觀的文化或部落可以在線下實現,並且新的物理場所可以由於意圖而不是隨機的機會而增長,該怎麼辦?
類似的想法已經在網路哲學界流傳了幾十年。 1988 年,法國社會學家米歇爾·馬菲索利(Michel Maffesoli)寫了一本名為《部落時代》(The Time of the Tribes)的書,認為下一個時代將看到更多的機構在由共同利益而不是共同歷史或血統和土壤定義的群體中行使。最近,巴拉吉·斯里尼瓦桑(Balaji Srinivasan)撰寫了《網絡國家》(The Network State)一文,認為由共同利益定義的社區可以從純粹的在線討論論壇開始,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具現化」為面對面的中心。從經濟民主的角度來看,大衛·德·烏加特的菲爾斯主張跨國集團之間的文化和經濟合作,協調線上和線下。
作者稱之為家的虛擬跨國社群是加密貨幣空間,它是看待這些問題的獨特場所。一方面,它是一個「科技」產業。整個空間運行在先進的軟體和數學上,例如區塊鏈和零知識證明。用戶透過在電腦和手機上運行的應用程式與其進行交互,這些應用程式接收透過互聯網提供的資料。
但它也有很多自己獨特的特色。與其他通常在舊金山或有時在紐約市周圍整合的科技行業不同,加密貨幣奇怪地抵抗了地理中心化的引力。以太坊的合法總部位於瑞士,第二個主要實體位於新加坡。它的許多開發商都在柏林。主要開發團隊位於羅馬尼亞和澳洲等地。一個第2 層擴展協議位於印度,另一個位於中國。
從某種意義上說,以太坊已經是這些數位網路部落之一。它已經透過在世界各地舉行的定期會議頻繁地「實現」,並且每次都吸引了成千上萬的人。這些為參與者提供了定期面對面互動和偶然聯繫的機會,而無需獲得美國簽證或支付天價租金。連續幾週,以太坊社群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人文地理,而不僅僅是回應。
Zuzalu 的開始
到了2022 年,我已經思考其中許多主題有一段時間。我閱讀並回顧了Balaji Srinivasan 關於網路國家的書,撰寫了有關加密城市可能會是什麼樣子的文章,並探討了DAO 等區塊鏈原生數位結構背景下的治理問題。但討論似乎太理論化太久,進行更實際實驗的時機似乎已經成熟了。 Zuzalu 的想法由此誕生。
Zuzalu 是將這些想法提升到一個新水平的實驗。我們已經有了黑客之家,黑客之家可以持續幾個月甚至幾年,但通常只能容納十到二十人左右。我們已經開過會議,會議可以容納數千人,但每個會議只持續一週。這時間足以進行偶然的會面,但不足以建立真正深度的連結。因此,讓我們朝兩個方向邁出一步:創造一個可容納200 人、持續兩個月的臨時迷你城市。
這達到了一個最佳點:它足夠雄心勃勃,與已經令人厭煩地重複的內容足夠不同,我們實際上學到了一些東西,但仍然足夠輕,在邏輯上是可管理的。而且它也有意不集中任何關於應該如何做這樣的事情的具體願景,無論是巴拉吉的還是其他的。
這項工作從一月開始。一個由大約四人組成的團隊開始勘察地點並決定在黑山建造一個度假村。度假村的價格通常相當昂貴,但一次性租用一百套公寓的議價能力,再加上選擇度假村通常空著的淡季時間,使成本大大降低。
我們邀請了大約十幾位邀請者,他們邀請了更多的人,並在幾個社區中共享了申請表:以太坊社區,重點關注從事零知識證明、長壽和更廣泛的生物技術行業的開發人員和研究人員,和歐洲理性主義者。我們也聘請了「元」的研究人員和建構者:網路部落、網路狀態、社區建立和治理。到了2 月份,團隊規模擴大到約8 人,並迅速進行後勤工作。這是一個挑戰,但與現有度假村合作卻出乎意料地易於管理。
3 月25 日,活動開始,兩百位賓客迅速湧入。 Zuzalu「集中規劃」的部分從一開始就可以使用。我們與當地一家餐廳合作,根據長壽大師布萊恩約翰遜的藍圖菜單製作了自助早餐。這些餐點融合了布萊恩確定最健康的飲食和生活方式的理想與實用性的需求,例如堅持每人每天15 美元的預算。
在加密貨幣方面,0xPARC 團隊創建了Zupass,這是一種基於零知識證明的身份系統,您可以用它來證明您是Zuzalu 的居民,而無需透露是哪一個。這可以當面使用,也可以在線上使用,包括匿名登入Zupoll等應用程式。不久之後,我們把其中一間公寓的陽台變成了健身房。
然而,從那時起發生的事情完全是自下而上的。每天早晨進行冷水浴的傳統自然而然地出現,並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展壯大。小組開始獨立烹調自己的食物。一個月後,我們開始唱卡拉OK。一開始,核心團隊組織了一個配備高品質視聽設備的會議室,並創建了一個網頁,任何居民都可以使用該網頁來無需許可地預訂時段並舉辦自己的活動。很快,居民開始創造子活動,賽道開始出現。
總而言之,Zuzalu 感覺已經實現了其核心目標:它匯集了新的文化組合,感覺就像一座城市。
我們學到了什麼?
兩百人長期居住在一個地方的「形式因素」確實有效。人們願意來,幾乎所有來的人都表示他們很享受這種體驗。這反映了我後來在太平洋島國帛琉舉行的為期四天的區塊鏈會議上也經歷過的事情:該活動故意減少正式會議形式,而以非正式的聚會活動(spend-time-together activities)為主,許多與會者表示非常欣賞這種獨特的活動構成因素。
(註:譯者深度參與了帛琉區塊鏈高峰會,這趟旅程也啟發了關於啟動群島網絡的想法- Archipelago.Network 是一個探索實現自我主權的烏托邦式賽博空間,匯聚了世界各地尋求自我主權和數位自由的個體對於鏈上治理的探索,群島是一種組織世界和人群方式的隱喻,共存不是基於權力關係,而是從多樣性中汲取力量。)
隨著時間的推移,Zuzalu 持續時間的延長成功地創造了一種不同的心態。為期四天的會議是你生活中的休息,但兩個月的停留才是你的生活。至少對某些人來說,事實證明,幾百個人關心你所關心的事情所產生的規模雖小但高度集中的網絡效應確實可以取代全球特大城市龐大但更加分散的網絡效應。
在專注的愛好者社群內建立和測試一項技術的想法也被證明是成功的。 Zupass 一開始本質上是一款笨重的黑客馬拉松軟體,但透過即時使用和用戶回饋,可用性迅速顯著提高,比許多已有多年歷史的區塊鏈應用程式更可用。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種技術——作為一種社交技術效果最好——這在Zuzalu 也得到了迅速的改善。
我們還沒有完全達到開發一種成本更低、耗時更少的布萊恩·約翰遜極端長壽生活方式的目標,但我們確實取得了重大進展。具有濃厚文化成分的技術,同時開發新的軟體工具和新的人類習慣,可能非常適合這種方法。
也就是說,仍有大量實驗要做。加密支付是比特幣和以太坊社群長期以來的夢想,雖然存在但有限。甚至沒有人考慮用DAO 來管理Zuzalu,DAO 是個在區塊鏈上運作的去中心化自治組織。一個持續兩個月的200 人社區要么太短,要么太小,要么兩者兼而有之,這樣的事情才真正有意義。但這兩個夢想非常重要,未來的實驗,無論是由Zuzalu 社區還是獨立的衍生項目進行,無疑都會做出更一致的努力來實現它們。
Zuzalu 也成功地成為了一個高度國際化的社區:沒有一個國家的與會者人數超過三分之一;不出所料,排名前兩位的是美國和中國。這種多樣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是一種有意的策略,以避免被任何單一民族文化的內部鬥爭和過度行為所俘虜。就主題領域而言,Zuzalu 的多樣性較低:雖然非加密社群也出現並欣賞這種體驗,但以太坊社群是明顯的先驅。
但這也許並不是失敗:出色的多樣性並不是要平等地代表整個社會或人類,而是要從戰略上將原本不會互相關心的群體聚集在一起並建立橋樑。
還有哪些問題沒有解答?
這個實驗做得不太好的地方是清楚地展示了下一步的發展方向。巴拉吉的《網路國家》確實談到了美國和其他地方小規模「共產主義社會」的多世紀歷史,但也強調了一個宏偉的地緣政治願景:去中心化運動,這是一場二十一世紀的不結盟運動,在不自由和高度衝突的世界中保護自由。也許這樣的運動甚至可以為中國和美國不穩定的地緣政治兩極提供一個和平的替代方案,然而,Zuzalu 還沒有真正實現如此崇高目標的感覺。
許多文化運動——數位遊牧主義、加密無政府主義等等——一開始都興奮地發展起來,但後來逐漸穩定下來,成為全球政治和文化格局的一部分。它們是穩定的,甚至是重要的,但一旦它們的自然愛好者群體飽和,最終就不會改變世界。 「祖札魯主義」也會遭遇同樣的命運嗎?事實上,稍微降低野心並讓這種情況發生可能是件好事嗎?
很容易認為,目前形式的祖札魯主義(Zuzaluism) 注定是相當小眾的。 Zuzalu 所吸引的社區雖然令人印象深刻,但也存在明顯的偏見:許多與會者都很年輕,很少有帶孩子的家庭,來的人也只待了幾天,大約三分之一的與會者已經是數位化的遊牧民族。靠著補貼,很多錢不富裕的人也能來,但從人脈關係來看,他們還是相當菁英的。
更廣泛地說,許多證據表明,除非面臨像真正的征服戰爭那樣強大的「推動因素」,奪取自己的土地,否則以前靜態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很少會重新開始並遷移到某個地方別的。即使在俄羅斯,在當前戰爭開始後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口離開該國。當然,許多離開的人都是俄羅斯最優秀、最聰明的人,他們的職責是削弱侵略性力量,並為其他可能這樣做的國家樹立榜樣。但同樣明顯的是,大規模移民還遠遠不是重大地緣政治問題的宏偉解決方案。
所以這就留下了一個問題:我們該何去何從?歷史上有許多有意舉辦的中等規模和長期聚會的例子,雖然這些聚會不會顛覆世界,但仍會留下有價值的影響。大學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好先例——這是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先例,因為十年前我們中有多少人熱衷於透過Udacity 和Coursera 等線上MOOC 服務顛覆實體大學,但儘管如此,這也是一個未被充分重視的先例。
修道院是另一個例子。幾年前,哲學家薩莫·布爾賈(Samo Burja)問,鑑於許多軟體工程師已經賺了足夠的錢,現在渴望個人精神進步,為什麼沒有專門致力於完善軟體的修道院。最終,Zuzalu 社區確實有比創建大學和修道院更高的野心,即使它們比修復全球政治要低。無論如何,適用於新領域的模型很少是對之前任何特定事物的精確複製。
我自己的預測是,Zuzalu 將部分成為一個具有大學、修道院和數位遊牧中心等方面的結構。但它也將引入全新的活動,例如透過在專門的社區中進行測試來「孵化」新技術,包括社交技術。它也將透過成為各種新物理場所和新社會的未來建構者的聚集地,在「元」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也就是說,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許多道路尚未探索,甚至未知,因此旅程才剛開始。
維塔利克·布特林(Vitalik Buterin) 是以太坊的創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