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作者:Rachel O’Dwyer, Alex Estorick, Ana María Caballero
文章編譯:Block unicorn
Rachel O’Dwyer 的新書《Tokens: The Future of Money in the Age of the Platform 代幣:平台時代裡貨幣的未來》現已推出精裝本和Verso的電子書。
Alex Estorick:近年來,NFT(非同質化代幣)與投票權代幣一起逐漸受到關注。為什麼代幣突然變得如此重要?是否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或只是使用的語言發生了變化?
Rachel O’Dwyer:代幣一直是實體經濟的影子。在區塊鏈、比特幣或2008 年之後的任何貨幣實驗之前,我們擁有以各種形式發揮作用的代幣。我所說的「代幣」指的是比國家支持的貨幣有更多或更少的交換媒介。它們比貨幣“少”,因為雖然貨幣至少在理論上是可替代的——一歐元與其他貨幣相同——但代幣帶有附加條件;它們通常只能由某些人使用或兌換某些商品或在某些地方或在滿足某些條件的情況下。
以沒有酒類許可證的學生會酒吧使用的啤酒代幣為例,這些代幣有多個歷史案例。對於無法使用自己的錢的已婚婦女,有一些特殊的代幣。這些婦女透過商店帳戶、郵政匯票或無形的美元度日。同樣,還有救濟券、食物券和針對窮人的救濟金,因為現金在過去(現在仍然)是被視為對弱勢群體的一種危險的救濟形式。
在過去,有一些特殊的代幣旨在剝削工人,不僅透過工資關係,而且在贖回時也是如此——雇主用稱為「票據」的代幣向工人支付工資,這些代幣只能在公司商店以一定的價格兌換,由雇主設定。如果這聽起來很神秘,那麼今天亞馬遜向美國境外以及最近在印度的Mechanical Turk 工人支付亞馬遜禮品積分,這些積分與工人的身份相關且不可轉讓。
代幣也比金錢「更重要」。它們命名了交換價值,但也用於吹噓、炫耀、惡搞、控制、溝通、調查等等。希臘和羅馬在古代有很多類似貨幣的代幣例子,但也將交換和交易功能與司法、行政和公共功能相結合:如用於會計目的的代幣;作為股份和所有權的代幣;記錄債務和信用的代幣;授予進入秘密社團的代幣;透明度代幣;投票權代幣;遊戲代幣;以及作為聲望和吹牛的權利的代幣。
我發現如此驚人的並不是我們的代幣經濟有何不同,而是古代或所謂的「原始」貨幣與今天的代幣之間有多少相似之處。

現在代幣正在回歸並成倍增加。這有著許多原因。一是正如雅羅米爾所說,2008 年打破了有關金錢的普遍禁忌。人們開始質疑金錢是什麼、有什麼作用、它可以是什麼。他們開始想像其他替代性的交換媒介。其次,隨著平台開始發行類似貨幣的東西並在後台做類似銀行的事情,使代幣脫穎而出。 M-Pesa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一家行動電話公司(Safaricom) 在飽受通貨膨脹蹂躪的津巴布韋發行電話積分作為實際意義的貨幣。其中一些代幣的出現是出於必要——在沒有支付但存在相當強大的電話網路的情況下,當地用戶使用網路東西作為實際的支付、貨幣或匯款。
其中許多創新從地球的「南方」延伸到北方。如果說M-Pesa是一個例子,那麼另一個例子就是Q幣,它是由遊戲公司騰訊發行的,用於購買在線代幣的貨幣,它很快就成為實際的線上代幣,直到中國政府乾預並將其推入地下。
這兩點都很重要:對國家的不信任加上做類似銀行業務的平台的出現催生了代幣經濟。自大流行以來,我們也看到金融虛無主義的興起,促使人們在所有文化都成為網路文化的時刻採用和開發代幣。

Ana María Caballero:印刷和鑄造貨幣的系統講述了哪些歷史?創造新的價值體系會產生哪些社會影響?這些影響實際上具有包容性嗎?
Rachel O’Dwyer:很難回答這個問題,因為這些歷史都非常複雜。如十八世紀出現了一種奇怪的文學流派,瑪麗·普維稱之為「社會流通文學」。托馬斯·布里奇斯(Thomas Bridges) 的《鈔票歷險記》(The Adventures of a Bank Note) (1759-75) 和查爾斯·約翰斯通(Charles Johnstone) 的《Chrysal》 或譯為《幾內亞歷險記》(1760-65)都是透過金錢來敘述的。硬幣或紙幣講述了它在旅途中遇到的所有人的故事,以及它在傳遞過程中無意中聽到的對話。幾內亞的Chrysal 描述了它在殖民貿易網絡中的旅程,從北美到英國,再到荷蘭和德國。正如克里薩爾所說,金錢被認為具有「進入直接擁有者的內心並解讀他們生活中所有秘密的力量」。代幣見證了它周圍的一切。
我非常喜歡藝術家Cildo Meireles 的一件藝術作品,名為《插入意識形態循環:鈔票計畫》(Insertion into Ideological Circuits: Banknote Project,1970)。他將秘密訊息印在鈔票上——諸如“洋基隊回家”之類的反帝國主義長篇大論,然後將它們重新投入流通。
在這裡,現金就像一種原始社交媒體——每個人都使用但沒有人能完全控制的東西。
人們在這種媒體上刻下訊息,有時也很有趣,例如2015 年史波克博士(倫納德·尼莫伊飾)去世後,加拿大人將總理威爾弗里德·勞裡爾(Wilfrid Laurier)的形象改為看起來像前者。但有時,這些資訊是政治性的,例如2019年的哈麗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 印章,美國公民在印有傑克遜總統的頭像的20美元鈔票上,印下領導地下鐵路的女性頭像將前者覆蓋了。

在我來自的愛爾蘭,我看到過歐元紙幣的圖片,上面刻著「無國界:結束直接供給」的字樣——這是一種不人道的住宿制度,尋求庇護者在等待申請結果的期間被無限期地關在類似監獄的環境。將這些資訊刻在錢上比刻在牆上更重要,你不覺得嗎?這是對我們作為對一個國家說話的東西,也是對權力的回應。塔布曼印章的使用者將其描述為公民不服從行為。
1900 年代初,當女性尋求普選權時,一些便士硬幣上被塗上了「投票給女性」的字樣。我喜歡將婦女參政論者便士(最小面值硬幣)視為一種NFT。其他維多利亞便士的硬幣都是相同的,而婦女參政論者的硬幣卻是獨一無二的——刻有不同的價值觀和要求。
在代幣中,我還考慮了多個示例,其中社區嘗試創建附加有「其他值」的代幣:佔公共資源的代幣;維護的代幣;或旨在為環境破壞等負面外部性定價的代幣。我很高興最近在Transmediale 與Olúfẹ́mi O. Táíwò 交談,他的新書《重新考慮賠償》(2022 年)剛剛出版。我認為他在我們的訪談中非常溫和地指出,有時經濟學家和貨幣理論家會有點沉迷於將貨幣作為解決方案,而其實解決方案必須在帳本上發生!但也許答案不是嘗試透過市場或正確的代幣來解決這些問題,我們也不應該總是嘗試。

不易替換和/或可程式交換媒介的黑暗面是平台或狀態腳本將價值轉換為代幣。
我們在美國的SNAP福利中看到了這一點——一種救濟代幣,只能用於購買國家認為適合窮人的東西,包括特定種類的食物,但不能購買酒精或熟食、熟食店或衛生用品。這不僅是金錢的價值,更是價值的展現。面對CBDC(中央銀行數位貨幣)和平台發行貨幣的未來,具有價值和附加條件的代幣顯然令人擔憂,但其是否有操作空間;我們確定希望將什麼樣的價值編碼到交換媒介中?或者我們最好還是別管它?
代幣也著眼於嘗試創造新形式貨幣的歷史,將替代價值銘刻到我們的媒介中。我探討了時間銀行和滯期費等替代貨幣體系的歷史,以及它們在歐洲和美國早期無政府主義社區中的使用。大多數都是驚人的(有時甚至是搞笑的)失敗。創建新的經濟體或社會不僅僅涉及簡單地創造不同的代幣。通常,當經濟學家處理這個問題時,他們將其視為經濟問題——一個價格問題。當工程師或電腦科學家接近它時,他們將其視為建築或工程問題。很多時候,貨幣改革問題都是透過技術決定論的視角來解決的——如果你簡單地建立正確的區塊鏈或協議,正確的社會就會神奇地跟隨。但要重塑社會,光靠殺手級應用是不夠的。

Alex Estorick:在NFT 時代,貨幣代表什麼? NFT 似乎打破了藝術與貨幣之間的差異?藝術在社會中的功能是否正在悄悄改變?
Rachel O’Dwyer:Mckenzie Wark 的論文「My Collectible Ass」中有一個很好的細分,對於這個問題非常有用。隨著商業資本主義的興起和藝術市場的興起,藝術品才成為一種商品。藝術家也變得更加具有個性,其作品因其獨特的地位而具有價值。
如今,藝術品更像是衍生性商品;其價值較少體現在作品的物質或美學價值上,而更多體現在網路效應、炒作或圍繞其傳播的訊息中。
將價值視為對資訊或網路效應的賭注,使我們能夠超越藝術作為一種資產類別(因為藝術長期以來一直是一種資產類別),並思考與此類特定資產相關的日益抽象的金融工具。如今,藝術品轉讓時所出售的東西不再是物質的東西,而是權利和行為的體系。最近,藝術不再關注物理對象,而更關注圍繞商品傳播的訊息。在觀念藝術和NFT的經濟中,重要的不是作品本身的物質實體,而是圍繞著它流通的權利體系。
在Tokens文中,我講述了Dan Flavin證書在火災中受損的故事。弗拉文是一位概念藝術家,以其現成的螢光燈泡排列而成的雕塑而聞名。收藏家仍然擁有這些材料組合,但契約已被銷毀。儘管他們仍然擁有物質作品,但他們不再擁有Flavin——因為所有的價值都在契約中。這總結了我們現在所處的時刻。它告訴我們很多關於NFT 為何有價值的資訊。這真的很令人沮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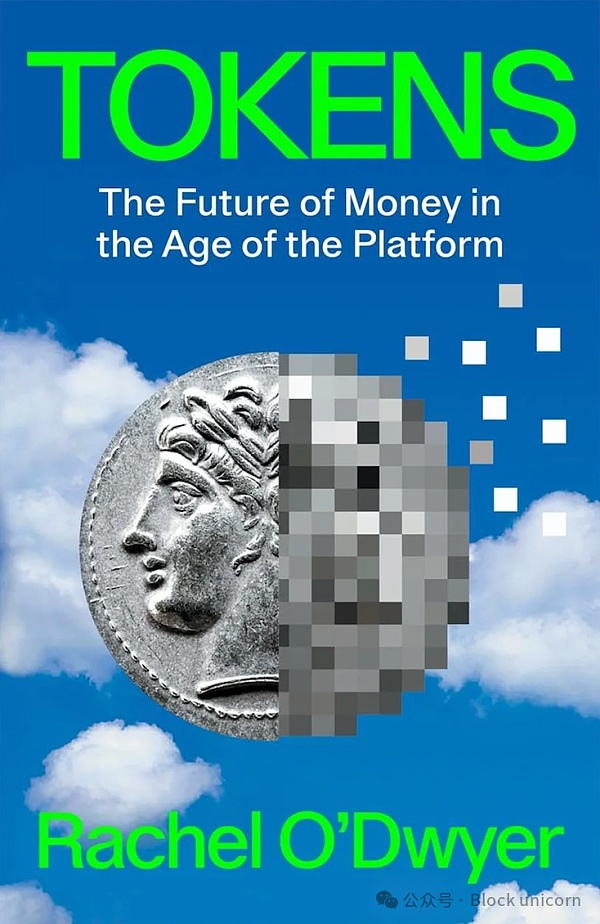
Ana María Caballero:在你的書中,你取笑了男性主導的加密貨幣會議,這些會議可能正在建立新的代幣經濟。如果一個新的代幣經濟主要是由男性建立的,那麼,用蘭登·溫納的話來說,這些新奇的人造物的政治意義是什麼?
Rachel O’Dwyer:我是因為激進主義傾向才開始賺錢的。但我很快就精疲力竭,幻想破滅。我對「倦怠」感到內疚,這聽起來好像我做了很多工作才達到這一點,但我沒有!我發現加密貨幣和貨幣活動空間的政治和氛圍令人疲憊不堪。在我二十多歲的時候,我和現在的我丈夫、他的妹妹以及其他一群可愛的人住在都柏林的一棟房子裡。這是非常包容的。一直有很多人往來。我們大多數人在日常工作之外參與了各種社會運動,無論是專注於反高檔化和反私有化等領域的當地團體,還是更多的全球計畫。
除了這一些東西之外,我的專長主要是數位共享,並且我參與了愛爾蘭以外的不同替代經濟項目。在2015年這段忙碌的時期,我接待了許多人,包括Robinhood、P2P 基金會的成員以及各種金錢活動人士。[…]我開始注意到科技激進主義中潛在的性別歧視,並覺得這很煩人。

Tokens文中有一個由金錢轉變為人權活動家的事件,雖然是為了搞笑,但實際上是一次相當令人不安的經歷。我被要求為一所大學組織一個關於金錢和公共資源的研討會。這份工作沒有報酬,我是唯一受邀的女性——我猜測是「象徵性的」女性。比約恩(Björn),我不會使用他的真名,因為他給我的印像是好訴訟的人,他非常咄咄逼人,並攻擊我說金錢激進主義對於非白人歐洲人來說也許不是最友好或最包容的地方。他說,也許歐洲白人男性不會覺得有必要訴諸歧視來證明自己的自卑。會議組織者在場,但沒有人採取任何行動來挑戰或化解局勢。
人們對互惠的想法有很多口頭承諾,但歸根結底,相同的舊等級制度或主體性被編碼到專案中。
我知道我也犯同樣的罪。我是在一種非常新自由主義的心態下長大的,我也帶著這種心態。我是一個糟糕的人,不願意告訴其他人如何重塑經濟,這就是為什麼Tokens的文中沒有真正就我們應該如何對待貨幣的未來提供任何規範性建議的部分原因。我知道我是不適合提出這個建議的人。但也許其他人可以在此基礎上提供正確的建議?

Alex Estorick:在Web3 中,共同創作和開源程式碼受到高度重視,但人們往往期望互惠互利。因此,它常常讓人感覺像是共享經濟和禮品經濟的混合。您從此類社區行為推斷出什麼?
Rachel O’Dwyer:我認為有這樣的風險:當我們使用任何類型的代幣來衡量互惠時,我們最終會過於密切地衡量貢獻。例如,在接受有關他們的經歷的採訪時,西科克的一個LETS(本地交易所交易系統)社區觀察到,與更非正式的交易所(例如酒吧中的“這是我的回合”)相比,交易中使用的帳本系統對個人貢獻的衡量有點過於嚴格(「你最近到底為我做了什麼?」)。
一旦我們引入會計系統或代幣——即使是以禮物或所謂的共享和共同商品的非市場意識形態為基礎的系統或代幣——就會存在一個問題:我們是否冒險將市場思維引入非市場或社會交流中。我們是否會冒著過於密切關注而無法給予和索取的風險?
市場和非市場交換之間、禮品經濟、貨幣經濟或共享經濟之間不存在嚴格的界線。所有的經濟關係都包含著社會關係,所有的社會性都包含著某種程度的計算。

Ana María Caballero:NFT 與歷史上其他類型的代幣有何不同?我們可以從前資本主義和非西方代幣經濟中學到什麼?
Rachel O’Dwyer:代幣不只是價值;他們溝通的不只是交換條款。他們也會開玩笑、連結和惡搞。令人想起NFT 奇怪的「吹牛權利」的是,中世紀法國的皇家代幣,稱為jetons royaux,其價值更多地與其圖像相關,而不是與其命名的交換價值或黃金重量相關。它們攜帶著一種內在語言——用符號包裹著不同層次的意義——大多數遇到它們的人都無法解讀。如果你能做到的話,那就代表你在某種程度上參與了這個笑話。
20 世紀90 年代,人類學家Viviana Zelizer探索了整個19 世紀和20 世紀通用貨幣如何從「指定用途」並轉變為專用代幣。在此之前,從馬克思到齊美爾,貨幣社會學的大部分觀點都認為貨幣將每一次交換都簡化為一次交易,將每一個「事物」簡化為它的價格。 Zelizer表明,雖然金錢可以計算,但它仍然是一種深度社交技術。
透過改變通用貨幣的功能或外觀,簡單的支付可以變成情人的紀念品、款待、禮物或賄賂。
正如“比特幣”的圖像搜尋所證明的那樣,代幣被明確編碼為“金錢”。但它們的交流能力也超出了其交換價值。當這些代幣透過群組聊天和社群媒體流通時尤其如此。人們使用Venmo和微信支付等支付應用程式不僅是為了匯款,還可以與朋友開玩笑、惡搞名人,甚至騷擾封鎖他們的前伴侶。
在網路遊戲中,皮膚和表情(一種動畫反應)等標記實際上是貨幣,但它們也可以用來炫耀、侮辱或慶祝。 Bored Ape 和Friends With Benefits等NFT 是投資代幣,但它們也將精英群體的成員資格編入法典。與商品貨幣(其價值相當於黃金或白銀)不同,代幣的一個定義是,它們是一種交換媒介,其價值高於其製成的物質。
代幣的價值不在於它本身,而在於它所代表的意義。
代表與所謂「實際價值」之間的聯繫不僅是圍繞貨幣本質的最大問題。可以說,這是自二十世紀初以來關於意義的最大問題。代表與事物之間的連結就是語言、藝術和價值的關鍵問題的歸結。當西方國家放棄金本位時,當藝術家決定將大量生產的物品指定為「藝術」時,當後結構主義哲學家挑戰文字與事物之間的關係時,這個問題就出現了。但當我們試圖理解伊隆馬斯克推文的代幣「有價值」或柴犬網路迷因的代幣為何流行時,它顯然也在發揮作用。

Alex Estorick:代幣能否幫助挑戰文化的金融化,還是只是推動文化的金融化?
Rachel O’Dwyer:代幣是多義的,因此它們可以輕鬆挑戰金融化,也可以輕鬆實現金融化,儘管絕大多數時候它們都是用來啟用它的。有多個項目使用代幣來挑戰或質疑文化的金融化。
伊夫·克萊因(Yves Klein) 的《非物質繪畫感性地帶》(Zone of Immaterial Pictorial Sensibility) 是其中最受歡迎的作品,其中涉及以預先指定重量的黃金出售巴黎塞納河上的七個隱形“區域」。要購買作品,買家必須會見藝術家,並在某種專家證人(博物館館長、策展人或畫廊老闆)和其他兩名證人在場的情況下轉移黃金。然後,克萊恩將一半的黃金扔進塞納河,在那裡將無法挽回。然後,買家將獲得非物質區域的所有權證明。問題在於以下條款:克萊恩指出,為了真正擁有相關作品,買家現在必須燒毀該契約。只有這樣,他才是真正的主人。從此時起,該作品不再可轉讓。
接受代幣就意味著放棄所有權。擁有它就意味著放棄未來交換的所有可能性。當交換權失去時,還有什麼價值?當交換就是一切時,藝術還剩下什麼?
正如代幣可以成為入駐、囤積以及猜測非物質和物質價值的空間,它們也可以成為質疑我們想要的價值類型或詢問當所有交換或炒作結束後還剩下什麼價值的空間。

Ana María Caballero:人類必須外包信任——將其置於外部物件(例如代幣和合約)中,這對您意味著什麼?在Web3 中,代幣變成了合約,這讓一些人歡呼「無需許可」的出現。相信代幣化合約是「無需許可的」有什麼危險?
比特幣白皮書提出了「無需許可」合約這一著名的想法——無需許可是因為我們不再需要相互信任,因為我們可以信任程式碼。這是cypherpunk和extropian社群中的一個流行想法——這兩個90 年代的郵件清單對比特幣和智能合約的發展產生了影響。這些社群相信,透過信任一個簡潔的協議,你可以擺脫人類官僚機構、政治和對他人的信任的混亂。他們想用代碼取代政府,但這是對政治和政府實際意義的一種非常簡化的看法。
我們仍然需要人們參與其中,每當Web3 所謂的「無需許可」社群出現問題或出現爭議時,這一點就很明顯。解決方案不採用智能合約或代碼的形式;它採取鏈下異議和爭論的形式。
無需許可更多的是一種願望或意識形態,而不是歷史上或現在任何時刻都存在或實踐過的東西。但我們不得不問:「為什麼這個想法如此誘人?」 為什麼這些社群想要用簡潔的協議取代其他人?政治中的什麼——漸進式變革了、其他人,或者混亂的爭論——對Web3 的愛好者來說如此沒有吸引力?當彼得·泰爾在《自由主義者的教育》中寫到以各種形式逃避政治時,為什麼密碼朋克和外向主義者以及彼得·泰爾都沒有吸引力呢?
我在Web3 中唯一真正喜歡的項目是那些涉及人的項目,並且是高度脫鏈的。例如,Circles理論上是一個區塊鏈項目,但所有重點都集中在促進社區內存在的社會聯繫上,而技術只是支持它的支柱的一部分。在這種情況下,該技術可以是按鈕或區塊鏈,但重要的是人和信任網路。
Rachel O’Dwyer是都柏林國立藝術與設計學院視覺文化學院的講師。她是加州大學歐文分校和劍橋微軟研究實驗室的富布賴特學者,目前是都柏林三一學院網路與電信中心Connect 的研究員。她是《神經雜誌》的共同編輯,並為Convergence、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和倫敦書評等媒體撰稿。她策劃了許多活動、研討會和展覽,探索數位藝術、技術和價值的交叉點。
Ana María Caballero是第一代哥倫比亞裔美國詩人,她的作品探討了生物學如何界定社會和文化儀式,揭開了浪漫化母性的面紗,並對將犧牲視為美德的觀念提出了質疑。她是貝弗利國際獎、哥倫比亞何塞·曼努埃爾·阿蘭戈國家詩歌獎和鋼趾圖書詩歌獎等得主。她的作品已在國際上廣泛出版和展出。她是數位詩歌畫廊theVERSEverse 的聯合創始人。
Alex Estorick是Right Click Save 的主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