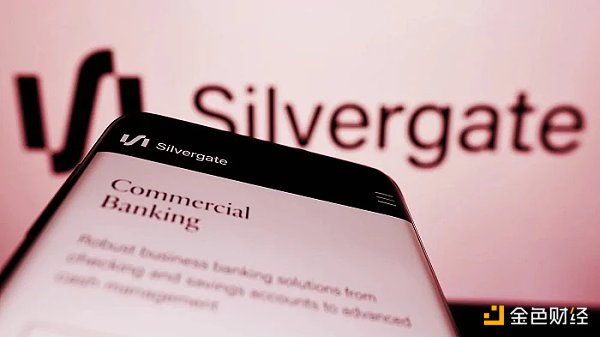來源:紅星新聞
隨著數位經濟的發展,“數位藏品”“虛擬貨幣”成了一些投資者的“財富密碼”,同時也暗藏風險。有不法份子以發行“數位藏品”為“幌子”,從事非法集資、詐騙等非法活動。紅星新聞記者註意到,已有一些地方公檢法部門對外公佈涉及「數位藏品」的刑事案件。
對此,曼昆律所主任劉紅林律師和劉正要律師接受紅星新聞採訪,分析了官方認定為非法集資罪或詐欺罪案件的五個特徵,並認為對外公佈此類案件,可以提醒消費者理性認知數位藏品的收藏價值。
五個數位藏品涉刑案件
一、 以劃分不低於300萬獎池等為噱頭引人入局
2022年11月,紅星新聞報導《數位收藏涉刑第一案!涉嫌詐騙資金265萬餘元律師:銷售數位藏品要避免觸及法律紅線》一文,提到河南商丘市公安局睢陽分局公佈了一起網絡平台涉嫌詐騙、公安機關已刑事立案的案件。該案涉及數位藏品平台,8名涉嫌詐騙的犯罪嫌疑人被當場逮捕。這起案件是當時官方部門公佈的第一起數位藏品涉刑案件。 2024年3月,紅星新聞從涉及該案的知情人士處獲悉,該案進入司法程序後,目前仍在審理中。
在睢陽分局公佈的這起案件中,經警方依法偵查查明:犯罪嫌疑人班某夥同畢某濤、期某思、班某圓等人利用網絡藏寶閣APP平台出售虛擬卡通圖片,以劃分不低於300萬獎金池、定期回購、現金獎勵、實體獎勵等為噱頭,涉嫌詐騙資金265萬餘元。
睢陽案受害者李先生是一名數位藏品愛好者,他同時在多個平台購買數位藏品,也活躍在一個有多名數位藏品愛好者的社群內。李先生買的數位收藏中,有的平台讓他賺了錢,也有的平台收藏價格下跌導致他虧錢。據李先生介紹,用戶在平台上購買了一定金額的收藏品後,如果藏品的價格出現了低於購買者購買的價格,用戶就會虧損。用李先生的話來說,藏寶閣和其他讓他虧錢的平台不同的是,「其他平台仍在運營,而藏寶閣的管理人員聯繫不上’卷錢跑路了’」。
二、開啟二級市場用「老鼠倉」套現獲利
根據紅星新聞記者發現,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就破獲了一起以發行「數位藏品」為幌子的詐騙案,抓獲7名犯罪嫌疑人,涉案金額200多萬元。蜀山分局民警透過調查發現,該平台公司其實是一個打著發行、交易“數位藏品”幌子的詐騙團夥,其謊稱所發行的“數位藏品”系“大師名作”,實際上都是來自一些普通畫手的作品,甚至直接從網路上截圖、拷貝的圖片,沒有任何收藏價值和實際價值,也無法適用於任何場景。公司營運團隊透過價格幹預、肆意炒作,以掌握內幕、承諾回購、限量發行等騙術造成飢餓營銷的假象,誘導投資者爭相買入,並在平台開啟的二級市場,渲染“數字藏品”的價值,利用投資客「追漲」的心理,鼓動投資客與投資客之間進行交易。
等到藏品的價格被迅速拉高後,該平台公司再將留下來的份額「空投」到自己的自持帳號上,冒充投資客將圖片以高價掛出,實現高位套現,同時關閉其他投資客的賣出通道,實現詐騙投資客錢財的目的。
蜀山分局警方已將該平台公司負責人、程式設計師以及客服人員等7人抓獲歸案,核實客戶端用戶100餘人,虧損共計250餘萬元,公司非法獲利40餘萬元。涉案犯罪嫌疑人已被採取刑事強制措施,案件正在進一步辦理當中。
三、虛增交易量營造交易火熱且有升值空間的假象
2023年11月,上海高院對外公佈由上海市閔行區人民法院(以下簡稱「閔行區人民法院」)審理的一起涉「數位藏品」的集資詐騙案件。在這起案件中,2022年6月,被告張某起意並與被告人劉某商議設立“通古平台”,利用區塊鏈技術將低價購買或從網絡免費下載的圖片包裝為“數字藏品」在平台上銷售,並謊稱平台是與官方文化協會聯合打造、並與多家博物館合作聯合發布的。平台也設定了一些特殊的規則,開放二級市場進行交易,還自買自賣,虛增交易量及價格,營造交易火熱且有升值空間的假象。
一波操作後,「通古平台」的關注度越來越高,張某、劉某也獲利頗豐,在收到用戶的錢款後兩人就陸續提現並分贓物。同年9月底,二人見目的達到,為逃避收益承諾和法律責任,張某停止伺服器續費,「通古平台」關閉,造成用戶無法提現、無法查看「數位藏品」。
據閔行區人民法院查實,該平台吸收數千名用戶資金共134萬餘元,造成被害人損失共41萬餘元。案件審理期間,二被告已退出全部違法所得。法院認為,被告張某、劉某以非法佔有為目的,使用詐騙方法非法集資,數額較大,均已構成集資詐欺罪,且屬共同犯罪。主犯張某犯集資詐欺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併罰金十萬元;從犯劉某犯集資詐欺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緩刑三年,併罰金十萬元。
四、安排多名業務員營造成功人士人設騙微信好友
在湖南婁底市婁星區人民檢察院公佈的一起案件中,該檢察院提起公訴的一起以投資數位藏品獲得高額返利的詐騙案宣判。 2022年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李某某安排多人作為業務員,增加好友營造成功人士人設。李某某購買用於詐騙的某數位藏品,並讓業務員在購買的該數位藏品投資平台註冊帳戶,向微信好友推薦該平台,宣揚該平台無風險,獲利高,吸引微信好友投資。欲待時機成熟則關閉該平台,將投資者的資金佔為己有。法院以詐欺罪判處李某某等7人二年二個月至三年十個月不等的刑期。
五、有人搭建黑平台騙錢被判刑十二年
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1月17日公佈的一起案件中,法院在審理案件時認為,陳某作為A公司唯一實際控制人,搭建不具備相應資質的涉案平台,發售不具有對等藝術、收藏價值的“數位藏品”,以誇大價值、承諾“保價回購”“贈送實物”等騙術,使客戶產生錯誤認識交付資金。後開放二級市場供用戶流轉交易,以拉抬價格等方式乾預、炒作,利用客戶「追漲」心理保持市場熱度從而歸集資金。陳某持續提現涉案平台錢款,用於個人消費及償還債務,並關閉平台造成客戶無法提現和查看藏品,導致案發時無法退還全部被害人損失的危害後果,可以認定陳某具有非法佔有目的。
法院認為,陳某虛構事實、隱瞞真相,騙取他人財物,金額特別巨大,其行為已構成詐欺罪。綜合考慮認罪認罪等情節,依法以詐欺罪判處陳某有期徒刑十二年,併罰金五萬五千元。該判決已生效。
數位藏品騙局五大套路
劉正要律師指出,我國刑法上的非法集資包括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和集資詐欺罪這兩個罪名。數位藏品涉及的罪名中,被官方認定為非法集資罪或詐欺罪的,通常涉及以下幾個特徵:
一是虛假宣傳,承諾升值,部分數藏平台在銷售數位藏品的時候會對外宣稱產品能夠升值,例如百分之三十甚至更高,或者承諾保底回購,如某個數字藏品的發行價為999元,平台承諾將來這個數位收藏的市場價格跌破發行價時候,平台進行發售價格回收。
二就是虛假上鏈,數位藏品具有唯一性,能夠真實上鏈,部分平台發布的所謂數位藏品並沒有真實上鏈,消費者購買之後不能在區塊鏈上查到。
三是老鼠倉或拉盤行為,部分數位藏品平台宣稱賣出1000份數位藏品,實際上對外只賣了400份,其中可能有600份都還在平台上。後期平台在二級市場上,透過各種宣傳造勢,例如消費者群裡有1000人,其中七八百人都是平台內部帳號,透過帳號之間的互動,營造某個藏品非常火爆的假象,從而炒高某個藏品價格,再將平台手上的600份全部高價拋出,平台獲得大量盈利,被拋售的數位藏品價格迅速下跌。
四是增發,平台對外宣稱為了提高數位藏品的收藏價值,只銷售1000份數位藏品,但市場上流通出來的卻有2000份。
五是平台販售的數位藏品畫作對外宣稱是某名家所畫,但實際上平台只是隨便找的某畫師,並不符合它的IP價值。
在上述涉刑案件中,被告被判刑的輕重程度不同,劉正要認為主要是根據涉案的金額來決定。劉正要提到,詐欺罪的量刑一共有三檔:第一檔,詐騙金額3千至1萬元(全國各省可以根據各省的經濟發展、治安情況等製定該幅度內的標準,江浙滬、廣東深圳等地區的立案標準是6千元),屬於刑法規定中的“數額較大”,可被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第二檔,詐騙金額3萬元至10萬元(多數地區都設置在10萬元),屬於刑法規定中的“數額巨大”,可被判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三檔,詐騙金額50萬以上,屬於刑法規定中的“數額特別巨大”,可被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
上海曼昆律師事務所的主任律師劉紅林談到,涉及刑事犯罪的數位收藏平台的負責人將犯罪的金額進行主動退還,那麼這一行為在定罪量刑這方面是考量的重要因素。
部分涉刑案件提到了平台開通二級市場,劉正要提醒說,一級市場是指發售的市場,是平台與用戶的交易,二級市場是指平台開通了寄售市場,所有的用戶都可以在平台上面進行買賣,用戶之間、用戶和平台都可以進行交易。開通了二級市場並不一定構成犯罪,只是開通了二級市場以後,會更加利於平台方進行集資詐騙等不法行為,對於用戶來說,風險會較大。劉正要律師進一步解釋說,在二級市場中,部分平台方會假裝買家或賣家帳號在市場裡參與交易,這類帳號的體量較大,平台方很容易透過這種方式去收割其他的普通用戶。
如何勘破數位藏品騙局
一、購買前需確認平台八項資質
面對層出不窮的數位藏品交易平台,劉正要提醒用戶在購買數位藏品之前,可以在網路上查看平台的資格要求,包括:
1.合法有效的營業執照;
2.平台網站的ICP備案及許可;
3.開通網站必須備案;
4.開通二級市場所需的EDI許可證;
5.數位藏品上鏈所需的區塊鏈資訊服務備案;
6.藝術品經營單位備案;
7.網路文化經營許可證;
8.拍賣經營批准證書。
二、數位藏品需有真實知識產權
除此之外,劉正要提到,發行人或平台合作的IP方均需要對發行的數位收藏有真實的知識產權,即使平台使用AI生成的圖片來鑄造,也要關注AI平台對於生成圖片的智慧財產權的權利聲明。目前來說多數平台並未授權或轉讓任何的知識產權類權益給用戶,用戶在購買此類數位藏品之前,可以去相關合作方的對外宣傳網站或帳號上搜尋相關信息,查看是否是真實合作。
曼昆律師建議
在實踐中,常被問到數位藏品的刑事案件涉及到的被詐騙資金能否要回的問題,劉正要表示,被司法機關追回的財物是可以依法返還的,但實務中因為很難全額追回用戶的投資款,例如用戶投資款被犯罪嫌疑人揮霍,一般情況是依照用戶購買時的投資比例回饋。
劉紅林進一步提醒,如果平台被判定為確實存在詐騙的犯罪嫌疑,那麼用戶第一時間就需要去報案,將相關經歷、證據、在網絡上查詢的公司基礎信息等材料作為報案證據,在律師的協助下做書面資料的刑事控告。除此之外,劉紅林認為,部分用戶採取的維權方式不合理,反而會給自己帶來不必要的麻煩,劉紅林說,也有用戶將數位藏品發行公司的負責人、員工的個人資訊在微信群或者公眾號上呈現,這樣的行為可能會涉嫌到侵犯公民隱私權、名譽權等。
相關部門將典型案例和犯罪的具體情況進行公告,對於整個數位藏品市場來說,有一定的啟示意義。劉紅林認為,對外公佈此類案件,可以提醒消費者理性認知數位收藏的收藏價值。此外,對於數位收藏發行者來說,也是正向引導,可以對發行平台的某些營運模式和對外宣傳內容進行風險提示。
為了加強風險防範,劉紅林認為監管機構在准入資質方面需要有一個引導性的標準,官方發布的涉及合規經營資質的指導文件,對於行業發展而言是有價值的。其次是消費者和平台的糾紛,監理機關需要一個合理的因應機制,雙方的權益都需要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