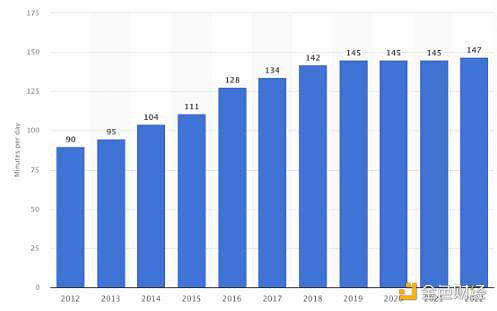此前已討論過OpenAI在股權投資協議設計獨特性,今天分享的是,OpenAI技術模式創新背後的創新機制的建立和創新文化的培育問題。
文:FT中文網專欄作家鄭志剛
農曆兔年伊始,生成式AI聊天機器人ChatGPT的顛覆式體驗代替了以往年節的傳統話題,成為親朋聚會和微信群聊的趣事。隨著一些互聯網大廠競爭產品的推出日程的排定,和國內一些創投領軍人士紛紛宣布加入人工智能研發計劃,一個AI新時代呼之欲出。畢竟,連比爾•蓋茨都說,ChatGPT的意義不亞於計算機和互聯網的誕生。
儘管未來發展仍面臨諸如科技倫理、商業化落地等諸多挑戰,甚至不排除ChatGPT成為下一個“網景導航者”(互聯網普及前曇花一現的瀏覽器領域先驅)的可能性,但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那就是它正在,甚至已經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
除了基於深度學習,利用生成式來形成人工智能研發技術的突破,從而完成技術模式的重大創新,推出ChatGPT的OpenAI在支持這種技術模式創新背後的企業製度設計也做了很多創新。圍繞OpenAI在股權投資協議設計的獨特性,我在FT中文網2月6日推送的專欄文章中已經集中做了討論。今天我想和讀者分享的是,支持OpenAI的技術模式創新背後的創新體制的建立和創新文化的培育問題。
那麼,OpenAI的異軍突起究竟為中國創新體制的建立和創新文化的培育帶來哪些有意思的啟示呢?
第一,破除產業政策的迷思。
很多學者用“ChatGPT以一己之力改變了全球人工智能領域的踟躕狀況”來評價它帶來的人工智能領域的重大突破。而推出ChatGPT的OpenAI源於2015年成立的一家致力於學術研究的小型非營利性實驗室,總部位於舊金山教會區的一家舊行李箱工廠。
即使在OpenAI於2022年11月30日推出這款ChatGPT之前,其實很多人連做夢都不會想到,這麼快人類社會就進入人工智能時代。事實上,這恰恰是創新帶給我們的魅力所在,它不是可控的,甚至是不可預期的。
讓很多人感慨的是,OpenAI沒有拿美國政府產業政策下的大基金投入的扶持和政府一分錢的財政補貼,僅僅依靠市場的風險投資的支持,在阿爾特曼和布洛克曼的帶領下,潛心研發七年,最終使ChatGPT橫空出世,脫穎而出。
我理解,美國科技成功的關鍵在於充分調動科技人的好奇本性(阿爾特曼和布洛克曼都有名校輟學的經歷),依靠市場的力量(風險投資的盈利動機),因而創新是持續的。馬斯克(帶著特斯拉到中國投資設廠)走了,阿爾特曼又來了,如此不斷。反觀中國,很多人或濃或淡具有某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情愫,那就是寄希望於出台類似芯片的產業政策和舉國體制,在有為政府乾預下實現“彎道超車”。
創新的不可控和不可預期的本性決定了這不是產業政策的製定者可以先知先覺的。很多時候,產業政策支持的選擇性反而扭曲了市場識別潛在項目的內生機制,增加了創新競爭的不公平性。歷史地看,也許只有市場和時間才有能力真正識別一個項目是否成功。 OpenAI其實只是眾多探索未知項目的初創公司中十分幸運的一家而已。中國需要的是一個真正包容的創業環境。這些對於創新導向的企業而言也許比產業政策扶植和政府補貼重要得多。
第二,走出公益願景的誤區。
最近在微信朋友圈我不止一次看到朋友們轉來的一張描述OpenAI“股權架構”的黑色圖片。除了像很多媒體那樣介紹OpenAI利潤分配的四個階段外,這個圖片特別強調,創始人兼CEO阿爾特曼是0股份,“原因是OpenAI成立之初對自己的定位是非營利組織”。這類“一群偉大的人用自己的錢去做公益造福人類”的描述無疑為OpenAI平添了許多神聖崇高的色彩,這使得對於很多初創企業而言,這家企業看上去有點高不可企。
同樣在微信朋友圈,我不止一次地回復轉來上述圖片的朋友,“這個不准確”。很多人(包括這張圖片的作者)都是從尚未上市的有限責任公司組織構架來理解OpenAI,但它其實是一家有限合夥企業(參見《推出ChatGPT的OpenAI股權投資協議設計的獨特性》)。 OpenAI是全稱為OpenAI LP的有限合夥企業。 OpenAI Nonprofit是這家有限合夥企業負責合夥人事務的普通合夥人(GP)。其員工也作為有限合夥人的一部分,因而阿爾特曼是有股份(更準確的說法是合夥份額)的。只不過從目前披露的有限信息,我們無法知道他究竟持有多少。
除了阿爾特曼本人或多或少是有股份外,鑑於巨大的研發投入無法依靠有限的捐贈的事實,OpenAI被迫走上商業化的道路,儘管其負責合夥人事務的普通合夥人叫做“OpenAI Nonprofit”,翻譯成中文為“OpenAI非盈利”。 OpenAI的這次內部轉型一定程度導致了最初致力於學術研究的小型非營利性實驗室的原始團隊的分裂。但商業化道路選擇至少從目前看並沒有改變阿爾特曼和布洛克曼創立OpenAI的初衷。這集中體現在他們的股權投資協議中第四階段,即在利潤達到1,500億美元後,微軟和其他風險投資者的股份將要求無償轉讓給OpenAI Nonprofit,用於實現“確保創建和採用安全有益的通用人工智能,造福全人類”的使命。顯然,他們這裡是用商業手段最終實現公益願景。
儘管這個社會需要以造福全人類為目標的理想主義,更需要通己達人的公益活動,但這些不應該成為人類福祉增進的主要實現方式。在現實中依靠公益願景,遠不如追求利益,同時基於專業化分工,借助市場服務社會來得更加有效。企業家主觀是為了追求自己的商業利益,但客觀上就會推動了人類社會的進步。這正如亞當•斯密曾經說過的,“我們每天早上可以吃到新鮮的麵包,不是由於他的仁慈,而是由於他的貪婪”。喬布斯、馬斯克等從商業目的出發完成的很多發明創造同樣可以造福人類。在這一意義上,我們也許並不需要苛責這些企業家是否應該保持公益的初心,而只需要他們依然保持過去是,現在是,未來還是對利益的追求就足夠了。當然,企業家能在追求盈利的同時,兼顧公益動機無疑對人類社會的貢獻更大。
事實上,如果我們可以把OpenAI的公益模式理解為“一群偉大的人用’自己的錢’去做公益造福人類”,這裡也提醒讀者,我們應該對一些人“用別人的錢,甚至是大家的錢”謊稱做公益造福人類保持習慣的警惕。我個人認為,OpenAI的公益願景在中國目前階段不具有模仿性,甚至簡單模仿可能會帶來災難。原因是,只有利益也許才能成為一個商業組織創新更讓人願意相信的理由,否則我只能簡單懷疑他們是騙子。
我們知道,公益的初心對於部分偉大的人會成為持續不竭的內在動力,但對於大部分人而言則需要外在激勵。公益和利益在現實生活中將不可避免地發生衝突。目前OpenAI的商業轉型也恰恰表明這種衝突的存在。這是我對他們這樣的模式究竟能走多遠的擔心背後的原因。因而在技術模式上做出重大創新的OpenAI如何在未來持續公益的願景,一路走下去依然充滿不確定性和挑戰。
這裡也衷心祝福OpenAI能像商業模式和企業製度創新一樣,在平衡公益和利益二者的關係上也走出一條新路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