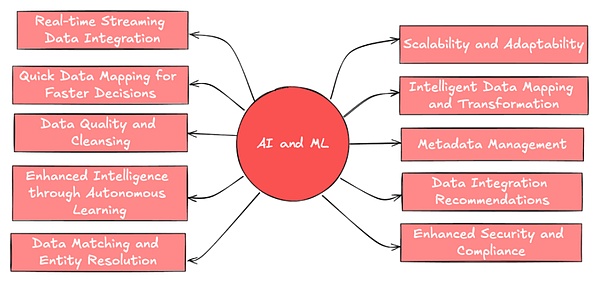引言:隨著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牽頭聯合十部委共同發布的《關於整治虛擬貨幣“挖礦”活動的通知》與中國人民銀行牽頭聯合十部委共同發布的《關於進一步防範和處置虛擬貨幣交易炒作風險的通知》的出台,標誌著我國虛擬貨幣市場已經徹底進入“強監管”時代,人們對虛擬貨幣的合法性、合規性、虛擬貨幣市場監管措施以及“幣圈涉刑”問題的關注度越來越高。
那麼,對於公司中管理虛擬貨幣賬戶或者負責計算機信息系統運行的維護人員,其非法佔有虛擬貨幣的行為能否構成職務侵占罪?本文將對這一問題進行探討,希望可以為司法實踐提供參考。 (本文討論的為狹義上的虛擬貨幣,即加密貨幣,不包括遊戲幣、Q幣等虛擬貨幣)
一、虛擬貨幣是否具有刑法意義上的財物屬性
討論侵占虛擬貨幣是否構成職務侵占的前提是討論虛擬貨幣是否屬於我國刑法意義上的“財物”。根據筆者的檢索結果,目前司法機關對此並沒有統一觀點,現存否定說和肯定說兩種觀點:
否定說。認為虛擬貨幣只在虛擬世界中具有虛擬的財物屬性,而在現實世界中不具備財物屬性,其只是一串數據或電子信息。目前,刑法對財產權的保護僅限於有形財產和無形財產,還沒有將虛擬貨幣(虛擬財產)作為財物納入進來,最高人民法院傾向性意見認為虛擬貨幣屬於計算機信息系統的數據,不具有刑法意義上的財產屬性。
肯定說。認可虛擬貨幣的財物屬性,具體理由如下:第一,雖然虛擬貨幣“不由貨幣當局發行,不具有法償性與強制性等貨幣屬性,不是真正的貨幣,不應且不能作為貨幣在市場上流通使用”,但是一方非法佔有虛擬貨幣一定會導致另一方失去佔有,其仍屬於刑法意義上的“公私財物”;第二,在刑事案件中,當事人均是看中虛擬貨幣的財物價值或經濟價值,虛擬貨幣在現實中是用真金白銀進行兌換的,其本身就具有相應的現實價值。如果刑法對虛擬貨幣的財物屬性不進行保護,那麼會導致大量犯罪滋生,在該領域刑法就會失去威懾力,公民的權利就不會得到保障;第三,2021年5月由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中國銀行業協會、中國支付清算協會發布的《關於防範虛擬貨幣交易炒作風險的公告》明確“虛擬貨幣是一種特定的虛擬商品”,即使目前虛擬貨幣交易被認定為非法,但沒有否定虛擬貨幣的商品屬性,商品屬於財物的範疇,那麼虛擬貨幣自然也屬於財物的範疇;第四,虛擬貨幣是一種電磁數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條規定“法律對數據、網絡虛擬財產的保護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很明顯立法者將數據、網絡虛擬財產納入到了民法所保護的客體範圍,為保證法律內部的一致性,刑法規定的財物範圍應等同於民法規定的財物範圍。
筆者認為,雖然否定說認為在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則下,刑法還沒有將虛擬財產納入保護範圍,但是立法本身俱有滯後性,社會關係是不斷動態變化的,法律從出台的那一刻起便“落後”了,當時的立法者只會針對當時的社會現象制定法律,無法預料未來,所以若僅以舊時的立法本意來評價當代的虛擬貨幣進而認定其不屬於刑法意義上的財物,筆者認為不具有合理性。虛擬貨幣屬於狹義上的虛擬財產(廣義上的虛擬財產包括遊戲幣、遊戲裝備等),將虛擬財產解釋為財物不屬於類推解釋,財物的含義可以完全包括虛擬財產,不違反罪刑法定原則。而且,筆者認為若單純的將虛擬貨幣作為數據進行保護,一律以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定罪處罰,等同於將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作為“口袋罪”,會導致罪責刑不相適應。 (筆者對此問題會在後文統一論述,在此僅作出簡要分析)例如,甲準備了50萬元用於購買比特幣,但在購買前被乙竊取,乙用竊得的50萬元購買了比特幣,後被丙竊取。根據現有的法律規定,乙的行為構成盜竊罪,量刑在有期徒刑10年以上;丙若構成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罪,量刑在有期徒刑3年以上至7年以下。同樣是盜竊價值相同的財物,這樣的處理方式明顯違反罪責刑相適應原則。而且,正如筆者前文所述,為保證刑法的威懾力,將非法佔有虛擬貨幣的行為認定為財產犯罪,才能更好地保護公民權利。若否定虛擬貨幣的財產屬性,那麼將會導致詐騙、敲詐勒索、甚至是搶劫虛擬貨幣的行為逃脫刑法制裁。筆者認為,雖然有觀點認為虛擬貨幣屬於“不合法物”,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虛擬貨幣不屬於財物。比如:淫穢物品、毒品等物,雖然屬於“不合法物”,但是其仍然具有財物屬性,仍具有經濟利益。
但筆者對肯定說關於“刑法與民法關於財物的定義應保持一致”的論據並不支持,北京市人民檢察院高級檢察官陳禹橦認為:雖然民法權利與刑法法益具有“同源性”,但在法益不斷變化的當下,對於新出現、值得保護的法益,刑法不是只能等待前置法全部“釐清捋順”後才能介入,刑法的謙抑性是就刑事立法與刑事司法觀念而言,不意味著刑法的調整對象、調整範圍和規制方式從屬於民法。
筆者註意到,從虛擬貨幣的定義來看,虛擬貨幣是“依據特定算法,通過大量計算產生的,具有流通性、匿名性和去中心化特徵的數字貨幣”,其同時具有數據、財物等多種法律屬性,不能簡單的將其認定為數據或者財物而否認其他屬性,可以將其看作具有多重屬性的權利集合體。
二、釐清職務侵占虛擬貨幣與盜竊罪、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的界限
因目前司法機關對虛擬貨幣的性質認定並不統一,導致實務中辦案機關對罪與罪之間的界限模糊不清,筆者對此進行簡單梳理和論述,希望對司法實務有一定參考價值。
(一)職務侵占罪與盜竊罪
將職務侵占虛擬貨幣與盜竊虛擬貨幣進行對比的前提是,職務侵占罪與盜竊罪均為侵犯財產類犯罪,也就是說認可了虛擬貨幣的財物屬性,認為虛擬貨幣屬於刑法所規定的“公私財物”。那麼,職務侵占與盜竊之間的區別就在於客觀方面,職務侵占要求行為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本單位的財物非法佔為己有,數額較大的行為。在此應注重對職務的理解,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職務上所具有的自我決定或者處置單位財物的權力,而不是利用工作機會。例如,利用其掌握公司交由他操作的虛擬貨幣賬戶權限的職務便利,竊取虛擬貨幣,其涉嫌構成職務侵占罪,但若僅僅利用工作便利竊取公司的虛擬貨幣賬戶和密碼則涉嫌盜竊罪。簡單來說,雖然本質上兩者的行為模式均為未經公司同意“竊取”虛擬貨幣並實現非法佔有目的,但職務侵占罪要求行為人本身因職務而控制公司的虛擬貨幣賬戶,而盜竊罪則不要求行為人利用職權控制虛擬貨幣賬戶,行為人也可以不是公司的員工,盜竊罪對行為人的主體身份沒有要求。
(二)職務侵占罪與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
同樣是行為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本單位的虛擬貨幣非法佔為己有的行為模式,對虛擬貨幣屬性的不同認定就可能導致司法機關在法律的適用上出現偏差。
筆者前文已經闡述過虛擬貨幣的財物屬性和數據屬性,若認為虛擬貨幣屬於刑法意義上的“財物”,則上述行為模式應認定為職務侵占罪。若否認虛擬貨幣的財物屬性,僅僅認同虛擬貨幣的數據屬性,將虛擬貨幣看做是一串數據,那麼就不應該以職務侵占罪進行懲罰,看似符合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的規制範疇,應該以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定罪處罰。筆者經過檢索發現,類案(2019)浙03刑終1117號案刑事判決書中,審判法院採用了上述觀點:以太幣作為一種特定的虛擬商品,與金錢財物等有形財產、電力燃氣等無形財產存在明顯差別,將其解釋為刑法意義上的“公私財物”,超出了司法解釋的權限……以太幣是依據特定的算法通過大量的計算產生,實質上是動態的數據組合,其法律屬性是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依法屬於刑法“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所保護的對象。
但筆者認為,審判法院以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定罪量刑存在不妥之處,在此以職務侵占罪為對比進行簡要分析。
第一,混淆了虛擬貨幣與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關於“數據”的含義。筆者認為,首先要確定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保護的是哪些“數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危害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刑事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明確入罪條件為:(一)獲取支付結算、證券交易、期貨交易等網絡金融服務的身份認證信息十組以上的;(二)獲取第(一)項以外的身份認證信息五百組以上的;(三)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二十台以上的;(四)違法所得五千元以上或者造成經濟損失一萬元以上的;(五)其他情節嚴重的情形。也就是說,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保護的是網絡金融服務的身份認證信息,具體來說是“指用於確認用戶在計算機信息系統上操作權限的數據,包括賬號、口令、密碼、數字證書等”。虛擬貨幣具備數據的屬性,但是明顯不具備身份認證信息的屬性。
第二,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所保護的是數據的安全,不是數據的歸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研究室負責人就《解釋》的出台背景答記者問題:“近年來,網絡犯罪呈上升趨勢,我國面臨黑客攻擊、網絡病毒等違法犯罪活動的嚴重威脅,是世界上黑客攻擊的主要受害國之一……製作銷售黑客工具、倒賣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和控制權等現象十分突出。”從中我們可以認為,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的設立是為了保護數據、計算機信息系統的安全,防止受到黑客、網絡病毒的攻擊,並非是為了確定數據歸屬而設立的。
第三,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的客觀行為模式要求是“侵入”或者“採用其他技術手段”。從語義上看,公司因行為人的職權主動賦予其保管虛擬貨幣交易賬戶密碼的職責無法解釋為“侵入”;同樣,使用“技術手段”也可以成立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但即便對此進行擴大解釋,以職務行為保管公司虛擬貨幣交易平台的賬戶密碼,也不能解釋為“技術手段”。根據體系解釋,參考《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條第三款,“技術手段”應解釋為“侵入、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的程序或者工具”。
三、“涉幣”職務侵占罪犯罪數額的認定
若構成職務侵占罪,則需要非法佔有的財物達到“數額較大”的標準。在本文的框架下,就涉及到對虛擬貨幣的價值作出評估。筆者經過大量的檢索和閱讀發現司法實務對虛擬貨幣的價值評估並沒有統一的標準。故將筆者認為針對本文內容有一定討論空間的評估標準作出梳理,具體情況如下:
(一)以被害人購入價為參考
《關於防範虛擬貨幣交易炒作風險的公告》明確,“虛擬貨幣是一種特定的虛擬商品”,換言之,既然虛擬貨幣具有商品屬性,則被害人購買虛擬貨幣必要支出對價的資金;《關於辦理盜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被盜財物有有效價格證明的,根據有效價格證明認定”,則依據該司法解釋,被害人購買虛擬貨幣時的交易憑證記錄了被害人獲取虛擬貨幣時支付的對價,可以作為證明虛擬貨幣價值的證據。該觀點把虛擬貨幣直接看作是一般的商品,跳過價格評估環節,客觀的體現了被害人的實際損失,可以更好地保護被害人的財產權益。
(二)以當天的平台交易價格為參考
該觀點的核心在於虛擬貨幣的價格是不停在變化的,且沒有規律可循。而虛擬貨幣與實物不同,其價值於時間沒有線性關係,不存在折舊、損耗等問題,沒有人可以預估其未來的價值,也許今天還停留在歷史高位,明天價格直接腰斬。筆者提出假設,如果被害人的虛擬貨幣是在歷史高位時買進的,但是行為人非法佔有時虛擬貨幣已經下跌,其價值大幅度縮水。那此時讓行為人以處於歷史高位的虛擬貨幣價值承擔責任,是否合理?或者被害人在歷史低點買進,在行為人非法佔有後虛擬貨幣價值上漲,又該如何確定其犯罪數額?正因為這樣的問題出現,考慮到虛擬貨幣的特質,在認定虛擬貨幣價值的時候應以行為人當時的眼光來看待。雖然虛擬貨幣在國內的相關交易被打上“非法”標籤,但是在國際市場上仍然被認定是一種金融商品,與股票類似,那麼對犯罪數額的認定以犯罪時的價值認定為宜。筆者認為,以行為人非法佔有時的交易價格為參考可以體現出行為人犯罪行為的罪責,實現罪責刑相適應。
(三)非法佔有後將虛擬貨幣轉賣的,以實際轉賣價格為參考
目前,因國內關於虛擬貨幣的政策導向問題,認定“虛擬貨幣無真實價值支撐,價格極易被操縱”,以平台交易價格為參考難以評價行為人的危害程度,不具有客觀性和普遍性。因為只有將虛擬貨幣兌換為法幣,行為人才能在“現實中”獲利,所以行為人在非法佔有後將虛擬貨幣變現的數額,可以一定程度上體現出虛擬貨幣的客觀價值。經筆者檢索發現,(2021)粵03刑終192號案刑事判決書中審判法院便採用了這個觀點,將行為人的變現獲利數額認定為職務侵占虛擬貨幣的量刑數額。
(四)非法佔有USDT等穩定幣的以當天美元與人民幣的匯率為參考
相較於比特幣、以太坊等虛擬貨幣,USDT作為穩定幣其因本身性質的原因,始終與美元在1:1左右的兌換比浮動,不會有較大的價格波動。其價值較為穩定,以該標准進行量刑,客觀性、合理性可以得到保障,也容易獲得當事人認可。公益訴訟檢察官雷瑤認為:“如果在交易中使用該幣種,對違法所得金額,我們仍然可以按照該幣種交易市場價值進行計算違法所得金額。”對違法所得,可以參考交易當天相關交易平台交易價格及美元與人民幣的匯率計算。筆者經過檢索發現,(2021)魯1302刑初1460號案中,公訴機關指控:“……竊取該公司受託管理的QYBB交易所的數字資產USDT75750個,價值51.991萬餘元。案發後,被告人鄭姝妍退還被害單位5043個USDT(價值約為34800元)……”。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不僅量刑數額以該標準為參考,行為人退賠的數額也是以美元與人民幣的匯率為參考標準的。
除上述參考價格之外,還有以“挖礦投入”、“平台均價”等標準為參考的。但是筆者認為上述兩個標準不具有合理性、客觀性,簡要分析如下:
若以“挖礦投入”為參考標準,首先“挖礦”行為本身就處於“危險”地帶,《關於整治虛擬貨幣“挖礦”活動的通知》明確“…嚴禁投資建設增量項目,禁止以任何名義發展虛擬貨幣“挖礦”項目;加快有序退出存量項目…”“嚴格執行有關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嚴肅查處整治各地違規虛擬貨幣“挖礦”活動”;其次,成本無法估計且沒有統一的衡量標準,難以量化,比如,當地電價、購買設備的價格、設備的折舊、時間成本、人力成本等多種變量不同,就會導致最終得出的結果不同,且司法機關會因鑑定過程的複雜而浪費大量司法資源,得出的結果也難以說服各方。
若以“平台均價”為參考標準。筆者認為,首先要考慮的問題就是如何選取時間區間和數據,這本身就是一個主觀考量,選取的數據可能會摻雜人的主觀意志,這樣又如何能保證結果的客觀性;其次,受政策影響,虛擬貨幣的價值忽高忽低,就像計算平均GDP一樣,將筆者和首富放在一組數據中計算平均數,得出的結果明顯難以客觀展示筆者為數不多的“資產”。還有,虛擬幣的交易平台不止一個,各平台的用戶、交易量、交易價格互不相同、互不相通,就導致走勢參差不齊,不然也不會有那麼多“搬磚狗”了。那麼,選取哪個平台才算客觀?很明顯,這又是個主觀選擇的問題,所以筆者認為以此為參考並不合適。
四、結語
本文通過對虛擬貨幣的性質、職務侵占罪的此罪與彼罪和對類案司法判例的分析,談論了侵占虛擬貨幣是否構成職務侵占罪。當然,針對涉虛擬數字貨幣職務侵占案件,根據案件實際情況,仍有諸多辯點,比如是否具有非法佔有的目的、案涉虛擬數字貨幣是否歸屬於公司(實踐中此辯點非常重要,且公訴機關很難舉證)、職務侵占罪與侵占罪的此罪彼罪問題等等。
雖然我國已經加強了對虛擬貨幣的監管,但是其炒作風險仍然較高,許多人被虛假的宣傳和高額的利潤吸引,不顧風險地參與其中。投資者不僅會面臨財物損失,還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責任。在此,筆者提醒廣大投資者要理性對待虛擬貨幣,遠離投機和炒作行為,謹防上當受騙。同時,希望一線司法機關能夠正視虛擬貨幣的多重法律屬性,避免對虛擬貨幣的單一看法。
參考文獻
[1]林胜超、林海珍:《非法轉移加密數字貨幣的刑法規制》,載於《中國檢察官》 2021年第18期6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