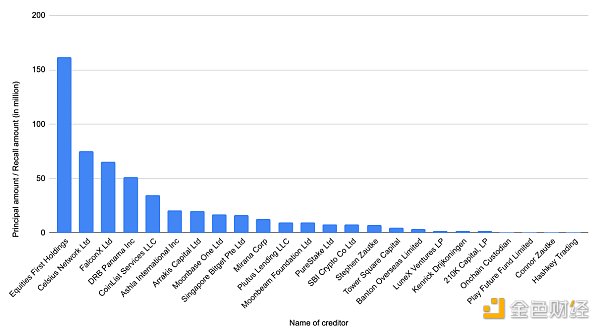近日,《中國檢察官》公眾號刊載了一篇北京市檢三分院檢察官撰寫的題為《非法竊取比特幣的刑法定性》(以下簡稱“《定性》一文”)的文章,文章認為,認定非法竊取比特幣行為性質,必須先解決比特幣能否成為刑法意義上財產的問題,即比特幣所附著的支配權益能否成為刑法所保護的法益。關於盜竊虛擬數字貨幣究竟應當以盜竊罪規制還是以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規制,近年來一直是司法實務界研討的熱門問題,筆者曾經在其他文章中談過,縱觀我國盜幣案件判決,呈現了盜竊——非獲——盜竊的轉變過程,目前各地多以盜竊罪追究盜幣者的刑事責任,比如文章中提到的朝陽區人民法院判決的盜幣案件,以及前不久上饒市廣信區人民法院判決的盜幣案件,等等。
從北京地區來看,關於涉虛擬數字貨幣類案件,海淀和朝陽辦理的相對較多,而北京三分檢作為朝陽檢察院的上級單位,最新朝陽盜幣案改判的裁判觀點與《定性》一文相呼應,作為關注虛擬數字貨幣刑事辯護的律師,更應當對《定性》一文仔細研讀,以期尋求對辯方有利的觀點。通讀全文後,有如下思考,亦或是困惑,求教於各位前輩同仁。
一、比特幣是否具有財產屬性?
2013年12月3日中國人民銀行等五部委《關於防範比特幣金融風險的通知》(以下簡稱“2013年《通知》”)規定“從性質上看,比特幣應當是一種特定的虛擬商品。”這是首次以部門規章的形式正向肯定了比特幣的“虛擬商品”屬性。而《定性》一文認為,2021年9月中國人民銀行等十部門《關於進一步防範和處置虛擬貨幣交易炒作風險的通知》(以下簡稱“2021年《通知》”)完全否定了比特幣的財產屬性。文章認為,2021年《通知》對比特幣等虛擬貨幣管控更加嚴格,將虛擬貨幣相關業務活動定義為非法金融活動,一律嚴格禁止,也即明確交易平台上比特幣的業務活動均為非法活動。延續了2017年《公告》精神,認定交易平台支配的比特幣無法作為刑法意義上的財產。
筆者註意到,無論是任何層級的文件,從來沒有否認過比特幣“虛擬商品”的屬性,即便是號稱史上最嚴監管的2021年《通知》。相反,2021年5月18日,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中國銀行業協會、中國支付清算協會聯合發布的《關於防範虛擬貨幣交易炒作風險的公告》中,再次明確“虛擬貨幣是一種特定的虛擬商品”。這裡的“虛擬”二字,並不是指價值虛幻或者法律性質虛假,僅是為了與傳統有形財產相區分。 《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條規定,法律對數據、網絡虛擬財產的保護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其中既包含數據,也包含網絡虛擬財產,那麼“虛擬商品”能否被認為是“網絡虛擬財產”?筆者認為,從一般大眾認知的角度來講,應當是可以的。老百姓不懂得那麼多的法律概念,只關注它是不是個“東西”,是“東西”的話是否歸我所有,以及我的“東西”被別人拿走了怎麼辦。
《定性》一文認為,隨著2021年《通知》的出台,個人支配的比特幣是否被國家認可,則需要根據國家監管政策精神進行解讀和判斷。文章提到,“個人純粹支配不用於任何交易的比特幣,此時比特幣不存在於被法秩序認可的交易之中,意味著其本身就不具有交換價值。其對支配人而言是否具有使用價值值得商榷,或者說即使比特幣能夠實現支配人一定的精神、感情滿足,但其使用價值也無法達到刑法保護的程度或者說沒有刑法保護的必要,無法成為刑法意義上的財物,無法具有財產屬性。”對此,筆者持否定態度。 2021年《通知》出台後,也有很多朋友諮詢個人持幣是否合規,筆者認為,針對當前政策,“幣囤不炒”肯定是完全合規的,也是應當受到法律保護的。如果認為比特幣不存在於被法秩序認可的交易中,不具有交易價值,那麼玩家在離岸做合規交易是否被法律所禁止?在其他國家的合法交易平台上是否具有交易價值?比特幣的價值並不僅僅限於囤幣和交易,如果使用比特幣作為消耗品在區塊鏈上做上鍊記載,包括使用比特幣網絡過程中消耗比特幣作為手續費,是否體現了比特幣的使用價值?筆者認為,比特幣的使用場景並不只有“交易”一種行為模式,也不只有在國內有交易場景,在以“法秩序認可”為要素考慮比特幣財產屬性時,應當具有國際視野和技術視野。
《定性》一文還認為,基於2017年9月中國人民銀行等七部門《關於防范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以下簡稱“2017年《公告》”),交易平台支配的比特幣不具有財產屬性,但個人間持有、交換比特幣的財產屬性未被否定(截至2021年《通知》前)。筆者認為,關於這個觀點,在實踐中存在諸多矛盾之處,或者說在實踐中難以操作和把握,須當知道,比特幣的持有或交易都需要載體,可以是錢包、交易所,亦或是通過私鑰、硬件等物理方式轉遞,既然認為個人持有的、交換的比特幣具有財產屬性,那麼個人存在於交易平台中的比特幣是否具有財產屬性?兩個自然人之間以交易所為媒介交易的比特幣是否具有財產屬性?即便是交易平台,其隸屬公司或實際控制人持有的比特幣存放於交易平台又該如何定性?即便是交易平臺本身的幣,其存放於硬件冷錢包中的幣已經脫離了交易平臺本身,又該如何理解?
二、關於盜幣案件按政策時間段區別定性是否合理?
《定性》一文認為,在明確了比特幣的刑法屬性的前提下,非法竊取比特幣根據行為手段、支配主體不同,可以分為三種情形予以認定,主要依據是政策時間段內比特幣是否具有財產屬性。 “如果行為發生於2017年9月之後,此時交易平台的比特幣不應認定為刑法意義上的財產,不能以侵財類犯罪來規制。”筆者認為,如前所述,交易平台中的幣並非歸平台所有,其實際持幣人仍是個人,既然認為此間個人持有的比特幣具有財產屬性,行為人盜竊了個人存放在交易平台中的比特幣,該如何定性呢? 《定性》一文似乎只考慮了幣在哪的問題,沒有考慮幣歸屬於誰的問題,如果按照文中觀點,仍應當定性為盜竊罪。包括筆者前文提到的具體情形,交易平台的幣存放於硬件冷錢包,而冷錢包通常由個人來掌管,按照文中的觀點,交易平台的幣不具有財產屬性,但實踐中基於個人持有的情況,似乎應當定性為盜竊罪,如此定性顯然與文義相悖,但實踐中此類情況恰屬普遍情況。
《定性》一文認為,“針對利用計算機信息技術非法竊取個人支配的比特幣的行為,如果該行為發生在2021年9月之後,無法以侵犯財產犯罪予以規制,應以非法竊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定罪。”筆者認為如此定性仍然存在先天缺陷,眾所周知,非獲的入罪標準有三種,損失、條數、獲利。基於虛擬數字貨幣領域的行為習慣考量,如果行為人利用計算機信息技術竊取了比特幣,但不做變現操作(實質上此種行為在幣圈極為常見),或者僅做幣幣交易,不做法幣交易,此時又該如何評價呢?獲利?沒有。條數?不夠。損失?眾所周知,非獲罪所稱的損失僅限於“包括危害計算機信息系統犯罪行為給用戶直接造成的經濟損失,以及用戶為恢復數據、功能而支出的必要費用”,按照幣的價值?與文義相悖,且通常來講不能認為是“直接造成的經濟損失”,作為個人通常無法舉證“恢復數據、功能而支出的必要費用”,則損失也不能認定,那麼以非獲罪追究盜幣者的責任,如何入罪?在此多說一句,實質上當前的非獲罪案例,所謂的“損失”都是被害人“做出來的”,比如發現被盜,找一家技術公司做個軟件維護升級等等,雖然不能說造假,但也並不符合刑法的精神內核。
三、如此定性,是否會引發新的問題?
筆者對於《定性》一文下述觀點持有異議:“竊取他人比特幣私鑰將比特幣轉移的行為。如果在2021年9月之後,則無法以侵犯財產犯罪予以規制,同時因手段行為等未能被其他如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等犯罪行為所評價,無法認定構成犯罪。”須當知道,刑法的基本原則包括法益保護原則,《定性》一文也認可,沒有監管文件明確2021年9月後個人持有比特幣的情形,但如果僅以此為由對盜竊私鑰的行為不做刑法上的評價,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意味著實質拋棄了持幣人的法益,比特幣不是物品,不能隨身攜帶,不能存在銀行,私鑰是虛擬數字貨幣的唯一憑證,如果對盜竊私鑰的行為不加以評價,那麼會不會引導行為人更加肆無忌憚的採取此種方式實施犯罪行為?筆者的擔憂並非沒有道理,隨著虛擬數字貨幣投資不受法律保護,已經湧現出了諸多的“幣圈老賴”,就是鑽政策和法律的空子,囂張的“欠錢不還”,同樣由於司法機關以虛擬數字貨幣不受法律保護為由拒絕立案,近期幣圈線下騙幣、搶幣案件持續高發。
如果按照《定性》一文的觀點,對於2021年9月之後發生的,行為人敲詐比特幣的行為該如何評價?搶劫比特幣的行為該如何評價?詐騙比特幣行為又該如何評價?如果比特幣是被害人2017年9月後一直合法持有的,並非因行為人加害而兌換的比特幣,豈不是同樣無法做刑法意義上的評價?顯然違背社會大眾的樸素認知。刑法的宗旨是懲罰犯罪,保護人民。正如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長張鵬曾談到,“數據犯罪說無法評價採用搶劫、詐騙等手段從被害人處獲取虛擬財產的行為。在社會公眾對於網絡虛擬財產與現實財產之間的交易轉換已經具備一定認知的基礎上,做此解釋不違背社會公眾的預期可能性與罪刑法定原則。”
四、關於比特幣,到底誰說的對?
從辯護律師的角度出發,《定性》一文的主旨思想實質上更加支持辯方觀點。在盜幣案件的辯護中,針對定性問題,辯護人基本會朝著非獲的方向去努力,例如筆者曾在浙江某地代理的盜幣案件,最終被告人被以非獲罪追究刑事責任,並適用緩刑。同樣的,針對涉幣類案件定性爭議,辯方可以以該文章觀點支撐己方觀點,實現罪輕辯護和無罪辯護。
《定性》一文的主旨思想,與最高人民法院的觀點是保持一致的。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部級專職委員胡云騰曾在某研討會中提到:最高人民法院主流觀點認為不能將虛擬財產等於財產,而應按數據處理。在罪刑法定原則下,虛擬財產(加密資產)還沒有進入刑法,其法律屬性是多元的,不能簡單等同於財產、數據或貨幣,宜將之作為權利束處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刑事處處長喻海松曾在某研討會中提到:在前置法律依據不明的情況下,具有財產屬性並不必然意味成為刑法上的財物,對相關行為不一定要適用財產犯罪。侵犯商業秘密罪的適用就是例證。同理,可以認為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的對象“數據”同樣可以具有財產屬性。在確實無法適用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等罪名的情況下,比如沒有使用技術手段而是直接敲詐勒索、搶劫虛擬貨幣的,也可以考慮通過手段行為予以評價;在極個別法益侵害程度高、社會危害大,手段行為確實難以罰當其罪的情況下,作為例外,可以考慮將行為對象解釋為財產性利益,嘗試適用財產犯罪定罪處罰。當然,這樣一個處理路徑實屬當下的“權宜之計”,系統妥當解決相關問題只能寄希望於民法等前置法的不斷完善。
實務中,支持應當將虛擬數字貨幣作為財產性利益予以保護的亦不在少數。例如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勞東燕認為:財產犯罪的構成要件應作與時俱進的理解和重構,財物概念也要做與時俱進的發展,以符合網絡時代的規範保護需求。將財物理解為權利束的發展傾向值得肯定,也符合歷史趨勢。鑑於無體物的物權屬性,對於部分可以財產犯罪予以保護的虛擬財產,應解釋為財產性利益。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黨組成員、副院長譚勁松認為:至於將虛擬貨幣認定為虛擬財產或財物是否需要法律予以明確,基於法無明文禁止即合法的基本理念,只要其具有財產特徵且法律不禁止個人擁有,就應視作財產而為法律所保護,法律認可與否不應成為障礙。上海市檢察院第二分院第三檢察部副主任吳菊萍認為:侵財類犯罪的打擊範圍也逐步擴大。根據司法解釋,刑法不予保護的財產,甚至是毒品等違禁品,從打擊特定行為的角度出發,也可以成為侵財類犯罪的犯罪對象。將虛擬貨幣解釋為侵財犯罪的對象面臨的障礙顯然更小。
五、結語
從來沒有一個事物像比特幣一樣,讓法律如此糾結。筆者認為,比特幣還是那個比特幣,僅僅因案件發生的時段不同,財產屬性若有若無,沒有體現出法律的可預期性,更會讓社會大眾無所適從,進而滋生新的法律問題。筆者文章提出的觀點或者疑問,也希望立法者能夠考量行業特徵和區塊鏈技術層面的問題。法律應當及時回應實務,針對虛擬數字貨幣,相關部門應當及時完善立法,亦或是通過兩高一部會談紀要等更為靈活的方式,對涉幣案件提供法律支撐,讓一線司法實務人員不再糾結。筆者關注到,國家外匯管理局管理檢查司副司長黃卉11月22日在2022金融街論壇年會上表示,共同推動完善虛擬貨幣等相關領域立法,加強虛擬貨幣的交易治理,按照不同類型不同功能將其納入非法支付結算,非法證券或者非法代幣等監管範圍。這應當被看作為積極的信號。誠如車浩教授所言,針對虛擬貨幣是否屬於財產,不存在本質主義的回答,國外相關規定參考價值有限,司法實踐也不能根據個別經驗進行歸納。對此應回到刑法基本原理,結合我國在不同階段的情況與法秩序變動進行判斷,對該問題的回答完全可能隨著時代發展和政策調整而不斷變化。
作者:劉揚
北京德恒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刑委會副秘書長、執業律師。北京大學軟件工程碩士。從事法律工作十五年,主要從事網絡、區塊鍊和數字科技與金融交織的細分領域刑事業務,網絡安全應急技術國家工程實驗室數據安全諮詢專家(國家級重點實驗室),北京計算機學會網絡空間安全與法務專委會副秘書長(楊芙清院士任學會會長),北京大學軟件與微電子學院校友會理事。聯繫方式:13581751329。
北京德恒律師事務所劉揚律師團隊成員普遍具有多年司法機關實務背景,持續關注泛crypto領域,擅長代理具有一定理據的涉幣詐騙、非法集資、組織領導傳銷、非法利用信息網絡、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案件的刑事辯護,涉幣民商事仲裁,元宇宙、nft、web3.0等新興領域行業合規及公司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