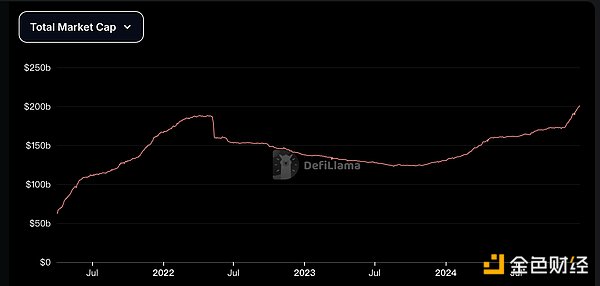24歲的楊壹,是那種最普通的縣城青年。高中輟學後,他跟著父母去了城裡的工地,也許會就這樣打上十幾年工,攢錢在老家蓋房、娶妻生子,然後回到工地繼續打工,像他的父親那樣。
但虛擬貨幣出現了,這是他人生里最大的變數。
楊壹跟著網上的人炒比特幣,玩的是合約,可以用槓桿“買幣”,並通過預測貨幣的漲跌,來獲得收益。對於沒有足夠本金的楊壹來說,這是一種門檻更低的玩法,但風險和機會同等大。
在互聯網上搜索“合約”,總會彈出“玩合約必死”的忠告。即便如此,還是有人狂熱地渴望在這場財富遊戲中淘金。比如楊壹。對於“暴富”的憧憬,像個深不見底的漩渦,將他一次又一次吸入幣圈。
在過去,他沒有能力也沒有運氣趕上時代的任何一班財富快車。如今,他沉迷這場以小博大的遊戲,以為自己終於能夠握住撬動財富、實現階層躍升的跳桿,儘管那其實是一把收割他的鐮刀。
一、“新大陸”
回憶起自己第一次點進虛擬貨幣的線上交易所,楊壹想到了潘多拉魔盒的寓言。打開虛擬貨幣這個“盒子”後,他的生活陷入一種麻木的循環:炒幣,欠下網貸,去工地還債。
但在當時,楊壹以為自己發現了一片“新大陸”。在交易所的衍生社區裡,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人活躍著,人們在這曬單、交流炒幣心得,或是開課傳授經驗。楊壹像剛踏入冒險遊戲的勇者,在社區裡接收“新手教程”。
那是2019 年。二月,比特幣的估值還是3500美元,等到六月他進入時,最高點已經漲破1萬美元。那枚看不見實體的貨幣,在短短四個月內身價翻了三番。
手握比特幣的屯幣黨,在這波春風中資產升值;部分合約玩家,通過對漲跌走勢的正確判斷,也實現了以小博大的翻倍。他們在社區裡曬出自己令人艷羨的資產截圖,在評論里相互恭維和請教。楊壹看著那些截圖里數得讓人眼花的零,第一次覺得,財富離人這樣近。
楊壹暗自欣喜,覺得自己發現了一條更容易賺錢的捷徑。更重要的是,這讓他有了離開工地的希望。
楊壹在高二的寒假輟學,去了父親所在的工地。他家位於貴州六盤水的一個小鎮,在那裡,像他這樣的人並不少見,他還在初中時,很多同級生就已輟學。去向也不多:在街上游盪;或者,離開小鎮到縣城找份工作;如果去更遠的地方,一般是戴上安全帽,投身大中小城市的基建事業。
建築工人的工作非常辛苦,有時,需要面對的危險更多。他去工地的第一年,父親從兩三米高的架子上墜落,膝蓋粉碎性骨折,躺了兩週。由於沒買保險,最後工頭只拿出了兩萬塊醫藥費,把這件事草草了結。
這使楊壹對工地生活產生了抵觸。接觸到幣圈後,他幻想自己也能像社區裡的那些玩家一樣,一夜之間擁有數倍資產。這樣他就可以擺脫那個滿是灰塵和噪音的世界,也終於有能力卸掉生活壓在父母身上的擔子。
工地上的架子,周圍沒有防護。上面站著兩個人,靠右的那個是楊壹的父親
他嘗試第一次投入,拿百來塊試水,玩的是合約。
合約交易,對應的是現貨交易。如果擁有足夠多的本金,可以直接買下貨幣、靜靜等待升值。這是較為保險的玩法,但對楊壹來說,靠屯幣獲利太慢了,也需要資金,像他這種手裡無錢的年輕人,直接被擋在這種玩法的門外。
而合約類似股票市場中的期貨,通過預測貨幣的價格漲跌來獲得收益。更重要的是,搭配槓桿,它可以將投入的本金翻倍,進而使收益翻倍。本金1萬,搭配100倍的槓桿買比特幣漲價,當比特幣的價格上漲1%,本金則實現100%的翻倍,直接獲利1萬。
但如果買錯方向,虧損同樣是100%的。比特幣價格只要下跌1%,1萬本金直接無影無踪。像這樣損失掉全部本金,被稱為“爆倉”。
在幣圈,許多人曾因市場動盪而頻頻爆倉,最終血本無歸。但也有人靠著操作和膽量,在高倍槓桿的加持下飛升,一夜暴富,成為傳說。
二、死在黎明之前
那些在合約市場里以小博大的故事,是楊壹迷上炒幣的開端。
白天,他隨師傅在工地干活,有空就打開手機,跟著活躍的老手學看漲跌的曲線,判斷貨幣之後的趨勢。晚上,他洗漱後仍不休息,在交易所裡進行合約交易。先把現金換成穩定幣,填入槓桿倍數,再判斷漲跌,買入還是賣出。每一個選擇都關係著這筆錢的結局:翻倍還是爆倉?
結局往往都是“爆倉”。在此之前,平台會提前預警,如果不及時追加保證金,本金就被“爆”掉;而交完這次保證金,也難保曲線下次的變數,最後常常與本金一併折損。

楊壹爆倉(即被強制平倉)後收到的郵件通知
失去最初的幾百元後,楊壹不甘心,覺得是自己技術不夠好。他操作更謹慎,但慾望在加大,投入的錢從幾百加碼到一千,槓桿倍數的單位從十升到百。銀行卡里的錢變少了,交易軟件裡的數字出現、增加,又再次歸零。
他幾乎被合約交易推著走。每晚,人就像懸在空中走鋼索,一顆心隨曲線的晃動而上上下下。資產的實時跳動讓他無法安心合眼睡覺,躺不了幾分鐘,又會起身拿手機。
炒幣不到一個月,他輸光了打工兩年攢下的四萬多存款。又欠下六萬網貸,才終於停止,只因拿不出再次入場的錢。輸到最後,楊壹沒有實感。唯一讓他不甘心的是,他失去了下一次入局的機會,那個“把錢賺回來”的可能。
楊壹終於理解某些合約玩家口中的“死在黎明之前”,他投入的錢幾乎每次都沒能撐過一夜。有次他累得握住手機睡著了,第二天醒來,錢已無影無踪,只有信箱裡留下“您已爆倉”的短信提示。
他很少賺錢。即使賺了,也總在等待它繼續上漲,最後等來一場曲線變向,錢連本帶利地爆掉。
現在,楊壹明白了,合約是屬於底層炒幣者的賭局。有錢人能拿出豐厚的閒錢投入,用小槓桿在裡面慢慢玩。而他們只能開著危險的倍數,拿存款、生活費,甚至靠借貸來搏一個“財富自由”的可能。這片大陸,不是他想像中的逐利場。
在幣圈的各種社群裡,楊壹見到許多被撕裂在生活與慾望之間的人。有人在裡面求助,問虧損後何去何從;有人寫下長文,反思自己如何走到今天這步。也有些留下跳樓訊息後就消失的人。他不知道這些人是否等到了屬於自己的黎明。
三、唯一的稻草
假如擁有錢、穩定的工作、一個屬於自己的家庭,楊壹覺得自己肯定不會再碰幣圈。但他一無所有,炒幣就像童話書裡的那根火柴,他忍不住一次又一次地劃亮它。
這個在幣圈搏擊的年輕人,在父母眼裡一直是個乖孩子的形象:安分、話少,做事穩妥。唯一沒聽從大人的那次,是他堅持要去縣城讀高中。
在他們高中,大概一半的人能上大學,多是二本或三本。他排在班里中等偏下,如果堅持到高考,或許也能考個三本。
可剛讀半年,他就想要輟學。與成績無關,只是單純覺得“讀書無用”,他把想法發在百度知道,被一個網友勸住,又多讀了一年。讀到高二,還是輟學了。 “身邊很多上了三本的同學,最後也沒什麼不一樣。”
在小縣城,生活的軌跡彷彿一出生就可以預見。
最直接的參照是自己的父親。初中畢業,父母就去了溫州的工地,他則獨自前往縣中,開始住校生活。工地一年能掙七八萬,為了賺錢糊口,背井離鄉去周邊的大城市務工,在當地是極其常見的選擇。許多縣城裡的孩子,更早地與父母分離,成為“留守兒童”。
但楊壹渴望能有一個溫暖、穩定的家,不想重蹈覆轍。在工地打了半年工,他開始尋找回到縣城的機會。先是回去征兵體檢,但他查出了“肘關節超伸”,被刷了下來。接著又在縣城歌廳裡找了份工作,但每個月只有兩千的工資。最後,他只好又回到工地。

在縣城的歌廳工作,楊壹形容自己“厭倦了這種暗無天日的生活”
人生走入了死局:像父母一樣在工地,就不能陪在家人身邊;想要回縣城組建家庭,月薪兩千顯然難以負擔;穩定的、收入滿意的工作,不會向這個沒學歷、沒技術的年輕人開放。
匱乏、絕望,加上一無所有的決絕,滋生了極大的慾望。儘管連續折損本金和貸款,楊壹始終無法停止對暴富的幻想。
2021年的夏天,楊壹第二次炒幣,虧損兩萬多。這使他產生了畏懼之心,“就感覺怎麼玩都是輸。”他刪除了所有的幣圈好友和交易軟件,決心不再炒幣。
當時他沒想到,自己退圈後不久,傳說便誕生了。
在幣圈,“涼兮”幾乎無人不知。這個名字總和三個數字綁在一起:519、1000、1000。
“519”是指2021年5月19日的虛擬貨幣暴跌事件,資料顯示,當天爆倉總額達到62.8億美元,約合404億人民幣。這天,在無數人棄倉逃生的同時,涼兮拿著1000元本金,用高倍槓桿滾倉到1000萬人民幣。當時他17歲。
所有人都沒想過,抓住這波歷史性大跌的,會是一個孩子。初始資金1000元,這幾乎是每個人都能達到的“開局門檻”。手持千元入場,成為千萬富翁,涼兮實現了這個近乎荒誕的可能。
儘管現在涼兮身上的千萬收益已變為負債,但至少在那一年,他得到了一切。暴富、流量,幾個交易軟件的創始人接連給涼兮送出夢想基金,獎勵他“越挫越勇的精神”。
就在一個又一個刺激中,楊壹的決心不斷鬆動。
四、跳桿與鐮刀
去年,他來到上海跟著朋友跑外賣,也是為了錢,他聽說“一個月能掙兩萬”。這是他離開縣城後去過的第一個大城市,在這座城市裡,外賣員像蜜蜂一樣跑來跑去。

楊壹在上海送外賣時拍下的,他覺得照片裡的人們像螞蟻一樣“各自忙碌又井然有序”
他二月來,跑得不夠快,沒賺多少錢。四月上旬被封控,一房間裡十個人,從早到晚地在美團搶菜。騎手們提前解封後,他和朋友住在橋洞,全城送菜。五月他把業務跑熟了,很少再超時。六月,他攢下了些錢。
慾望也許就是這時找上來的。 “去那邊就見識到更富有的生活。”楊壹停頓了下,“感覺差距太大了。”上海讓他對更好的生活產生了嚮往,跑外賣和乾工地都磨損身體,不是長久之計。環顧身邊的途徑,只剩下炒幣,一個可以被他自己抓在手上的跳桿。
六月下旬,楊壹第三次開啟自己的炒幣之路。第一天投入了五千,沒成。手頭還剩有跑外賣攢下的兩萬,是他全部的積蓄。
為了錢,他在封控期間四處奔波,出租屋回不去,他和騎手朋友們在公園或橋洞過夜。為了更多的錢,楊壹咬咬牙把它們扔進去。揮霍的速度超過他自己的預料,兩天過去,他虧得只剩下飯錢。

楊壹車上系滿了待送的物資
他很傷心,本打算到此為止,又覺得“要搞就搞大的”,於是傷心轉為一種決絕。恰逢手機裡的一個網貸軟件突然額度暴漲,他先是藉了五萬,後面又藉了三萬。事情發展到這裡已很難停下,他繼續下載別的網貸軟件,最終借了十三萬多。
7月1日,楊壹花光了這筆錢。上午十點半,他在朋友圈裡發了一個“廢”字,宣告這場博弈的結束。
期間他有想過停下,最後還是被自己說服,覺得已沒有退路可走。他總害怕收手後的下一秒會出現什麼大波動,收手便會後悔,不如把翻盤的希望押在下次開單裡,直至搏擊到最後,連手頭用來吃飯的700塊錢,他也會投進去。
“本來就覺得自己一無所有,才會想要去搏。”他說,“我越沒有那個機會,就越狂熱地想給自己創造機會。”
當炒幣成為一場財富遊戲,大部分人的動機,都是希望通過它發達。他們不知道閃電網絡是什麼,不懂得比特幣的分叉,又如ICO是哪三個單詞的縮寫。這些未能理解區塊鏈本質的普通投資者們狂湧進市場,成為炒幣“擂台”上最原始的搏擊者,同時也是匿名助推比特幣升值的被迫害者。
爆倉多次後,楊壹現在也承認,像他這樣的普通人入場,就是等著被割的韭菜。 “我們都知道自己是韭菜,但還是想在獅子裡面搶肉吃。”他把自己逗笑了。 “搶不到肉,湯也行。”
五、何處尋出路
去年他欠貸十三萬,催收的打電話打到了家裡。父母這才知道,在看不見的地方,他已走上另外的軌道。
對於這個小鎮家庭來說,十三萬負債並不輕鬆,母親第一次為他哭了,楊壹心裡難受。他聽從了父母的建議,安心回到工地上班,家人為他湊夠了那筆錢,解除了債務。
但楊壹不想一直呆在工地上。他輟學出來已有六七年,光是工地上的日子就佔據他近五年的青春。
“工地太危險了。”他邊說邊嘆氣。前年,他在一對兄弟包下的工地上做工。上一分鐘,工頭的哥哥還在和他聊天,下一分鐘,塔吊上的木板滑脫後掉到對方頭上,人沒了。高得可怕的塔吊,容易出事故的運貨車,工地上的鋼筋與坑洞,都讓他想逃離這裡。
在日記裡,楊壹這樣寫到:
工地是我這輩子的歸宿了麼,不會的,等我把傷治好了我還會再出來的。哪怕遍體鱗傷了,我也不想過一眼望到頭的日子。
今年他二十四歲,準備在工地干到過年,至於明年的打算,楊壹掰著指頭給自己數出:工地、進廠、跑外賣。 “但這三個都不是我想要的。”

前陣子,楊壹從工地下班,抬頭看見彩虹,這是他“第一次離彩虹這麼近”
去年年初,他交了五百學費,進入一個自考專科的學習群。老師把網課視頻發下來,讓他們利用自己的自由時間學習,完成後在群裡打卡。
楊壹堅持了半個月。跑外賣十點才下班,他就學到十二點,常常因為太累而睡倒在老師滔滔不絕的話語裡。他後面還是放棄了,覺得自己不是擁有“自由時間”的那類人。那門沒學完的思政課,已經不記得是馬原還是毛概。
對於他來說,最美好的日子可能停留在學生時代。讀高中時,朋友借了他一本巴掌大的小書,是關於比爾蓋茨的,楊壹放在枕頭下面,每晚讀幾十頁。高二輟學去工地前夕,室友們朝他開玩笑,說你也要去做比爾蓋茨?
他當時以為,未來就像商業書裡寫得一樣,處處充滿機會。出來後發現,一個沒學歷、沒技術的年輕人面對的世界,處處都是艱難。維持活著的狀態,已是很多人的全部。
在上海跑外賣時,有個比楊壹大十歲的騎手大哥,聽說他玩幣圈,跑來找他談心。大哥年輕時炒股,虧了四十萬,如今還在還債。 “這些東西不是我們能玩的。”他對楊壹說,“我們只知道怎麼把錢扔進去。”
但楊壹不是一個會就此甘心的人。當被問還會不會再炒幣時,他猶豫了會,略為無奈地說,如果有機會,應該肯定還是會去玩。他現在的桌面上,還留著幣圈軟件的專屬分類,裡面是一些交易所和資訊軟件,共有十個。心裡那點小小的希望,始終無法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