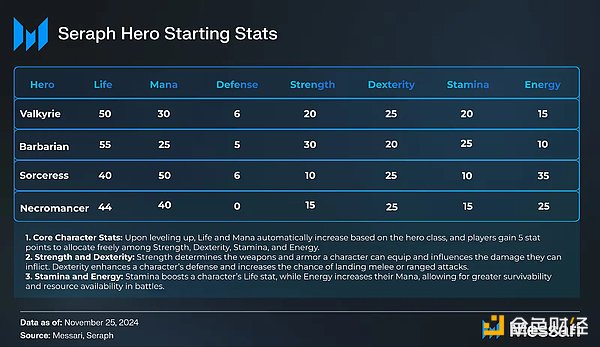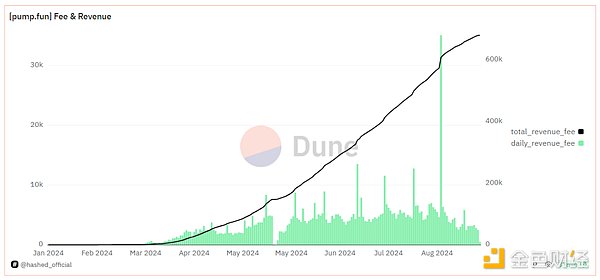01
案情引入
設定以下場景:
A某是B交易所平台上的一名普通用戶,B交易所是一家國際知名的數位貨幣交易平台,其總部位於境外,用戶可以在平台上進行市場買賣、限價委託、市價委託以及止盈停損委託,也可以透過平台的槓桿服務來實現數位資產的槓桿交易,也可以透過平台的合約服務實現數位資產衍生性商品的交易。最初,A某透過網路接觸了解到平台,並成為了該平台的一名使用者;之後,基於對該平台「推薦返傭」機制的信任,A某按照平台的操作要求,進行了所謂的「推薦「行為,並透過推薦他人使用該平台,獲取一定平台給予的回饋。 A某僅為平台的一般用戶,對於平台深層的運作模式和營利機制都沒有深入的了解,亦不屬於平台的管理人員。
之後,辦案機關將平台提供的合約交易服務定性為開設賭場罪,同時以涉嫌開設賭場罪的幫助犯為由,將A某予以刑事拘留。
02
平台提供合約交易業務,是否構
成開設賭場罪?
1.開設賭場罪相關法規梳理
1.《刑法》第三百零三條:以營利為目的,聚眾賭博或者以賭博為業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併處罰金。開設賭場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併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處罰金。
2.《關於辦理賭博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條:以營利為目的,在計算機網絡上建立賭博網站,或者為賭博網站擔任代理,接受投注的,屬於刑法第三百零三條規定的「開設賭場」。
3、《辦理網路賭博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辦理賭博案件意見》)第一條:【關於網路上開設賭場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利用網路、行動通訊終端機等傳輸賭博視訊、數據,組織賭博活動,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屬於刑法第三百零三條第二款規定的「開設賭場」行為:
(一)建立賭博網站並接受投注的;
(二)建立賭博網站並提供給他人組織賭博的;
(三)為賭博網站擔任代理並接受投注的;
(四)參與賭博網站利潤分成的。
4.《辦理賭博案件意見》第二條:【關於網上開設賭場共同犯罪的認定和處罰】明知是賭博網站,而為其提供下列服務或者幫助的,屬於開設賭場罪的共同犯罪,依照刑法第三百零三條第二款的規定處罰:
(一)提供賭博網站網路存取、伺服器代管、網路儲存空間、通訊傳輸通道、投放廣告、發展會員、軟體開發、技術支援等服務,收取服務費數額超過2萬元的;
(二)為賭博網站提供資金支付結算服務,收取服務費數額在1萬元以上或幫助收取賭資20萬元以上的;
(三)為10個以上賭博網站投放與網址、賠率等資訊有關的廣告或為賭博網站投放廣告累計100條以上的。
實施前項規定的行為,數量或數額達到前款規定標準5倍以上的,應認定為刑法第三百零三條第二款規定的「情節嚴重」。實施本條第一款規定的行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認定行為人“明知”,但是有證據證明確實不知道的除外:
(一)收到行政主管機關書面等方式的告知後,仍實施上述行為的;
(二)為賭博網站提供網路存取、伺服器代管、網路儲存空間、通訊傳輸通道、投放廣告、軟體開發、技術支援、資金支付結算等服務,收取服務費明顯異常的;
(三)在執法人員調查時,透過銷毀、修改資料、帳本等方式故意規避調查或向犯罪嫌疑人通風報信的;
(四)其他有證據證明行為人明知的。
5.《辦理賭博案件意見》第五條:【關於電子證據的收集與保全】偵查機關對於能夠證明賭博犯罪案件真實情況的網站頁面、上網記錄、電子郵件、電子合約、電子交易記錄、電子帳冊等電子數據,應作為刑事證據予以提取、複製、固定……對於電子數據存儲在境外的計算機上的,或者偵查機關從賭博網站提取電子數據時犯罪嫌疑人未到案的,或者電子資料的持有人無法簽字或拒絕簽字的,應由能證明提取、複製、固定過程的見證人簽名或蓋章,記明有關情況。必要時,可對提取、複製、固定有關電子資料的過程拍照或錄影。
2.我們認為,不宜將B平台提供合約交易業務的行為認定為開設賭場罪。
虛擬貨幣合約交易業務,指買賣雙方對約定未來某個時間以指定價格接收一定數量的某種虛擬貨幣資產的協議進行交易,交易所透過統一制定的標準化合約,設定虛擬貨幣或商品的交易種類、時間、規模,提供相關撮合交易服務,投資者可以透過判斷價格的波動方向,透過繳納保證金(虛擬貨幣),選擇買入做多或賣出做空,根據趨勢判定上漲或下跌的過程獲得收益。
我們認為:對於交易所平台的合約交易業務,平台提供該業務是否涉嫌開設賭場,應嚴格從犯罪構成和我國刑法的基本原則來進行分析:
首先,從犯罪構成方面來說,開設賭場罪要求行為人客觀上有經營賭場的行為,主觀上具有透過經營賭場牟利的目的。傳統開設賭場犯罪的行為人一般是基於營利目的,主要透過賭資抽成來牟取暴利;而本案中,平台除了透過提供合約交易服務的抽成來獲得獲利之外,同時也經營著對接掛單交易、限價委託等業務,與傳統賭場純粹因「組局坐莊而在賭資中按比例抽頭漁利」有很大的區別。
其次,從刑法的原則來說,我國堅持罪刑法定基本原則,即「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從平台所提供的合約交易業務所使用的虛擬貨幣性質來看,目前中國大陸法律對虛擬貨幣的定性是虛擬商品,暫未給出更明確的法律屬性。從境外前沿的學術研究來看,虛擬貨幣種類繁多,大多數學者傾向於從應用場景和適用功能來定性不同虛擬貨幣的法律屬性,如對ICO行為中的代幣更傾向於定性為證券;對比特幣(BTC)這種主流虛擬貨幣則較適合界定為物。從金融屬性來看,以比特幣代表的主流虛擬貨幣已在全球許多國家被認定為一種投資工具。
儘管目前我國法律暫不認可虛擬貨幣交易活動的合法性,但也並未將開設虛擬貨幣交易所提供合約服務的行為認定為開設賭博網站。並且,鑑於當前VR、AI等技術的受限,以虛擬貨幣作為重要激勵機制(Token經濟)的Web3產業仍在發展初期,虛擬貨幣本身的價值有待商榷,有專業人士認為,虛擬貨幣作為區塊鏈項目的激勵機制,對於發展區塊鏈項目和建構未來的Web3經濟意義重大,我國已將發展區塊鏈技術寫入國家經濟發展計畫、上升至國家戰略高度。當下,合約交易及虛擬資產正向價值尚不明確,隨著我國對區塊鏈和元宇宙、NFT等項目的大力支持,以及國際層麵包括香港、新加坡、倫敦等已開發國家或城市紛紛推出政策爭奪全球虛擬資產金融中心地位,未來我國對以虛擬貨幣為主的虛擬資產相關業務活動是否會在監管的框架內逐步放開尚有待觀察。
綜上,劉律團隊認為:對於合約交易業務能否定性為開設賭場的問題,應當嚴格遵守疑罪從無原則,不宜在沒有法律規定的前提下,將合約交易認定為“開設賭場”,並對相關業務活動予以刑罰手段規制,否則可能有違刑法的謙虛性原則。
03
為平台推薦用戶幫忙推廣的,就
都是幫助犯嗎?
我們認為:行為人A某作為平台的一般用戶,對案件參與程度與介入因素較弱,且不具備違法認識的可能性,不宜將其認定為開設賭場罪的幫助犯。
1.從客觀來看,A某是否構成開設賭場罪的幫助犯需要考慮其對於犯罪行為參與程度與介入因素的強弱。
我們認為,即使辦案機關認為平台提供虛擬貨幣合約交易服務的行為構成開設賭場罪,為平台推薦用戶幫助推廣的行為人也未必就構成開設賭場罪的幫助犯,而是要從多角度進行綜合分析,尤其要考慮行為人對於該平台涉案行為參與程度和介入因素的強弱。
行為人對於犯罪的參與程度強弱是判斷行為人是否構成幫助犯的關鍵要素。如果是中立的幫助行為,可替代性較高,應否定幫助行為與實行行為之間的因果關係。
從學理來看,華東政法大學孫萬懷教授等人發表在我國核心期刊《法學》的《中立的幫助行為》一文中所引案例:張某是一名出租車司機,兩名乘客李某、孫某搭乘張某的計程車,並且讓張某在城中兜圈,兩人上車後不久,就開始拿出毒品在出租車內吸食,張某發現後未作任何表態,仍然載著兩人繼續行駛。之後兩人不僅如數支付了車費,而且給司機張某多付了20元錢。後來兩人因為犯罪而被逮捕,並交代了在張某出租車內吸食毒品的情況。司機張某的運輸行為屬於正常的載客行為,對於乘客在車內吸毒的行為張某沒有義務去阻止。一般運輸工具不會成為吸毒的場所,運輸行為也不能導致吸毒行為的發生,出租車主要承擔的是運輸的職能,且張某的行為並沒有超過其本身行為的限度,沒有理由要求他有拒載或報警的義務,所以運輸行為與吸毒行為之間不具因果性,張某不構成犯罪。
從實務來看,前文所設場景中,B平台的推薦返傭機制在模式上與我國曾盛行一時的P2P平台高度相似:如果是P2P平台上的一名用戶,透過邀請他人掃碼或點擊自己發送的連結進行註冊等形式,為該平台拉新推廣,並取得平台給予的一定回饋金額。這只屬於平台的一種正常商業推廣行為,即使平台後續可能涉嫌非法集資等犯罪,對於推薦他人加入的平台用戶,不能要求其在推薦他人加入時,就知曉P2P平台可能存在的全部法律風險並對其予以審核,這顯然不符合正常邏輯下對平台一般使用者的期待標準。因此,顯然不宜將該類使用者定性為平台犯罪行為的幫助犯。同理,也不宜將上述場景中的A某認定為B平台所涉嫌的某些犯罪的幫助犯。
其一,從A某與B平台的關係來看:所設場景中A 某與B平台不存在任何勞動關係或勞務關係,不了解平台虛擬貨幣合約服務板塊的具體經營模式,也沒有參與到提供虛擬貨幣合約服務的具體行為中來。其二,從A某的行為特徵來看:A某作為B平台的普通用戶,與其他眾多用戶一樣,只是透過平台的某個機制獲取一些福利,其行為完全依照平台的操作提示,對平台的涉案行為不具任何支配性和操控性,這就類似於:P2P平台使用者透過邀請好友掃碼而獲得平台紅包,屬於一種正常的市場推廣行為。其三,從行為的不法性審查來看:在共同犯罪中,對幫助犯行為違法性的審查,需要結合其行為是否幫助了正犯的不法行為來判斷。在上述場景中,A某的行為最多屬於透過推薦平台給予他人,從而獲取平台給予的推廣返點,其從未幫助組織用戶在平台參與合約交易,亦不存在為平台提供資金、場地、技術支援、資金結算服務等情形,不宜以此認為A某的行為為平台開設賭場提供了幫助。其四,從產生的社會效果來看:處罰實際操縱犯罪事實的幕後指使者,能夠有效地抑制犯罪;但是,處罰一個對平台涉案行為無任何決定性、支配性作用的普通用戶的“推薦”或「邀請」行為,不僅難以起到預防犯罪的作用,反而會使眾多消費者不敢相信任何平台的推廣行為,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能會阻礙市場經濟的正常發展。
目前已有相關司法解釋體現了這種謙虛性精神,在《關於辦理利用賭博機開設賭場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七條中,明確了,「【關於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把握】重點打擊賭場的出資者、經營者。對受僱用為賭場從事接送參賭人員、望風看場、發牌坐莊、兌換籌碼等活動的人員,除參與賭場利潤分成或領取高額固定工資的以外,一般不追究刑事責任……」以上司法解釋所體現的指導精神符合當下社會的經濟發展趨勢,值得在司法實務中推廣。舉重以明輕,對於在賭場中僅受僱從事勞務性工作,不參與具體管理和分成的人員,尚不追究刑事法律責任,那麼,對於所設場景中,與平台不存在任何勞務關係,亦沒有領取平台高額利潤分成與固定薪資的普通用戶A某,其對B平台的合約交易業務只起到極微小的作用,無法支配掌控甚至參與相關行為進程,更不宜將其作為涉案行為的幫助犯而追究其刑事責任。
因此,我們認為:即使認為B平台構成開設賭場罪,A某在其中所起到的參與程度和幫助作用也很小,不能僅因為其幫助拉新推廣,就認為他是幫助犯。
2.從主觀來看,A某隻是基於對平台返傭機制的信任發展用戶,主觀上不具備違法認識的可能性。
根據《辦理賭博案件意見》第二條的後半段,對於開設賭場犯罪共犯的認定,要求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明知”,但這種“明知”的具體內容與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明知」有實質差異:後者只要求行為人認識到被幫助對像是在利用資訊網絡實施犯罪行為,但對具體實施的是何種犯罪行為則並不知情;前者則要求行為人必須明確認知到被幫助對象所實施的是網路開設賭場的犯罪行為。只有在有證據證明行為人實施了某些特定行為的前提下,才可以認定行為人對平台涉嫌的開設賭場行為具有「明知」的情形。
針對上述場景:其一,從對B平台合約交易業務的參與程度來看,如果A從未為平台提供網路技術支援、廣告投放、資金支付結算等服務,亦不曾透過平台向他人收取服務費,則其對B平台相關業務不存在刑法意義上的「明知」;其二,從對執法的配合度來看,在執法人員對B平台涉嫌開設賭場行為進行調查時,如果A某並未實施妨害調查證據或向平台相關人員通風報信的幫助行為,亦不屬於「明知」情形;其三,從主觀惡性程度來看,在A某被辦案機關刑事拘留前,若其不曾收到行政機關的任何告知,則也不屬於法條所述「收到行政主管機關書面等方式的告知後,仍實施相應行為」的明知故犯情節。其四,從違法認識的可能性來看,對於虛擬貨幣平台上提供的合約服務是否屬於開設賭場行為,法學理論和實務界的主流觀點一直是:建議嚴格遵守疑罪從無原則以保持刑法謙抑性。那麼,對於沒有學習過法學專業知識的A某,要求其註意到平台提供的虛擬貨幣合約服務屬於開設賭場的違法犯罪行為,並認識到其推薦給他人獲取返利的行為屬於幫助行為,是不符合現實生活邏輯的。因此,A某並不具備違法認識的可能性,只是基於對平台邀請他人推薦返傭機制的信任發展新用戶,不構成B平台開設賭場罪的幫助犯。
綜上,劉律團隊認為:在沒有充分證據證明行為人對平台開展涉嫌開設賭場罪的行為屬於「明知」的情況下,不宜認定行為人實施的「推薦」行為屬於平台開設賭場的幫助行為,從而追究其作為開設賭場罪幫助犯的刑事責任。
04
司法實務中,對於幫助平台拉新
推廣的行為,往往如何處理?
從目前的司法實務來看,對於行為人僅僅只是為平台推薦、邀請新用戶,幫助平台推廣,從而涉嫌犯罪的,辦案機關大多都從輕處理甚至不起訴。
例如,在【關檢刑不訴〔2023〕23號】不起訴決定書中,2020年2月至2021年6月,被不起訴人羅某某下載名為「愛遊貴州麻將」的賭博APP並註冊成為該平台代理,先後邀請其微信好友到該賭博軟體內以打麻將方式進行賭博,賭博平台每局收取玩家房費後,羅某某可從中獲得一定比例提成。案發後,羅某某經公安機關電話通知主動到案並如實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實,積極退繳其違法所得。本院認為,羅某某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零三條第二款規定的行為,但犯罪情節輕微,具有自首情節,積極主動退贓物,且自願認罪認罰,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十七條之規定,可以免除刑罰。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二款之規定,決定對羅某某不起訴。
因此,我們認為:即使A某構成開設賭場罪的幫助犯,結合具體案情以及當下的司法實務,也可以對其從輕處理甚至不起訴。
此外,在【鎮寧檢刑不訴〔2023〕58號】不起訴決定書中,2020年9月至2022年2月,被不起訴人田某某利用手機下載「馬鈴薯棋牌」APP,並創建了親友圈,陸續招攬鄒某某、劉某某等人在該APP上以打捉雞麻將的方式進行賭博並從中獲利。本院認為,被不起訴人田某某以營利為目的,利用網絡代理打捉雞打麻將的方式開設賭場,抽頭漁利,情節嚴重,其行為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零三條第二款之規定,已構成開設賭場罪。鑑於被不起訴人田某某具有自首情節、自願認罪認罰、主動退贓物,犯罪情節輕微。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十七條之規定,無須判處刑罰。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二款之規定,決定對田某某不起訴。
我們認為:鑑於本文所述參與交易所平台拉新返傭此類案件的案情創新性,對類似案件的處理應立足於案情本身,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從最大限度發揮刑罰的積極功能、實現刑罰的正義和預防犯罪的目的出發,慎重辦理此類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