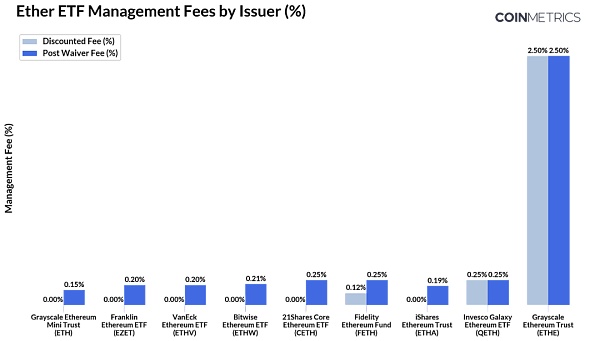尼可拉斯‧尼葛洛龐帝認為,網路將會「使組織走向扁平化,使社會走向全球化,也會使控制去中心化,同時也將使人群變得更加和諧」。那些身穿灰色法蘭絨套裝、充滿自信地漫步於工業時代走廊的古板男人們將很快消失,而他們的權威所依靠的指揮鏈系統也會隨之消失。尼葛洛龐帝和不少學者都論述過,取而代之的將是互聯網,「數位世代」將會崛起,他們喜歡玩樂卻能自給自足,心理健全像互聯網一樣,這一代人聚在起,組成了由獨立的個體聯結而成的協作式網絡。國家也會走向消亡,公民會從過時的黨派政治轉向去數位化市場中「自然」集會。而長期拘束於軀體中的個體也得以擺脫肉體的束縛,去探索他真正感興趣的東西,找到有共同興趣的伙伴。無所不在的電腦網路已經到來,從那些發光的連網設備中,專家、學者,以及投資人看到了一個理想的社會:一個去中心化的、平等的、和諧的、自由的社會。
但這是如何發生的呢?就在三十年前,電腦還是冷酷的工業時代社會機器的工具和象徵,而如今看來,電腦卻要把這部社會機器推向滅亡。 1964年冬天,在柏克萊參加言論自由遊行的學生就擔心美國政府會把他們當成抽象的數字。他們一個個拿著空白的電腦打孔卡,打上「FSM」(言論自由運動)和「Strike「(遊行)字樣的孔,掛在脖子上。有的學生還別了徽章在胸前,仿照打孔卡使用說明寫道:「我是加州大學的學生,請不要折疊、扭曲、旋轉或毀壞我」。對於那些參與言論自由運動的人,以及許多生活在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人來說,電腦就是一項反人性的技術,它代表了集中式的官僚架構,它使社會生活理性化。但是,到了1990年代,曾是冷戰時期技術專家治國象徵的機器又成為了轉變的象徵。在越戰結束20年,以及美國反主流文化運動開始消弭之際,電腦反而把反主流文化運動時期曾經提到的個人主義、協作社區,以及精神共融的夢想變成了現實。資訊科技所代表的文化意義變化得如此迅速,這是怎麼發生的呢?
有記者和歷史學家認為,部分原因是技術上的。到1990年代,冷戰時期那種佔據整個房間的電腦大部分都已消失。同樣,保密森嚴的用來放置這些機器的房間也不復存在,大批維護這些計算機的工程師也相繼離開。美國人已經使用了微型計算機,其中一些只有筆記本那麼大。而所有的這些,一般人都可以買到,不再是某些機構的特權。這些新的機器可以完成一些非常複雜的操作,遠遠超越了最初發明的數位計算機的運算能力。人們用這些新型的機器來通信,寫作,創建表格、圖片和圖表。要是透過電話線或光纖連接網路的話,可以用這些電腦給彼此發訊息,可以從全球的圖書館下載大量訊息,還可以將自己的觀點發佈到互聯網上。正因為電腦技術有了這些方面的變化,電腦的應用範圍更加廣泛,同時也使得社會關係類型變得更加豐富。
雖然這些變化都非常戲劇性,但是它們本身卻不足以帶來烏托邦式的改變。例如,電腦可以放在桌子上並被個人使用者使用,但這並不意味著電腦就是「個人」技術。同樣,人們可以透過電腦網路走到一起,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一定要成為「虛擬社群」(virtual community)。恰恰相反,肖莎娜·祖波夫指出,在辦公室環境下,電腦及電腦網路可以成為強大的工具,把個人更加緊密地整合到公司裡。而在家裡,這些機器不僅可以讓小學生從公共圖書館下載文獻,還可以把客廳變成電子購物商場。對於零售商來說,計算機可以幫助他們獲取潛在顧客各個方面的資訊。所有的那些關於網路崛起的烏托邦式的論斷,都沒有提到電腦或電腦網路可以把組織結構變得扁平化,讓個人在心理上變得更加完整,或者可以幫助分佈在不同角落的社區建立起緊密的聯繫。那電腦和電腦網路又是如何跟點對點( peer to peer)的靈活組織「扁平化」的市場,以及更為真實的自我這些想法聯繫上的呢?這些想法從哪裡來的呢?又是誰提出計算機可以代表這些想法的呢?
為回答這些問題,本書追溯了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主角是一群對後世影響極大的記者和創業者,他們是斯圖爾特·布蘭德(Stewart Brand)和“全球網絡”(Whole Earth Network )。 1960年代未至90年代末,在波希米亞文化下的舊金山與南部新興的技術中心矽谷之間,布蘭德組織了一群人和一批出版物,共同發起了一系列的跨界交流活動。 1968年,布蘭德把這兩個圈子的人聚集到了那個時代的標誌性出版物《全球概覽》。 1985年,布蘭德再次把兩個圈子的人拉到一起,這次是在「全球電子連線」(Whole Earth Electronic Link),簡稱WELL。而從19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布蘭德和《全球概覽》團隊的其他成員,包括凱文·凱利(Kevin Kelly)、霍華德·萊茵戈德(Howard Rheingold)、艾斯特·戴森(Esther Dyson)以及約翰‧佩里‧巴羅(John Perry Barlow),成為了網路反主流文化預言方面廣被提及的發言人。 1993年,他們又共同創辦了一本雜誌,比起之前的雜誌,這本雜誌用了一個更革命性的詞彙——「連線」( Wired )來描繪這個正在崛起的數位世界。本書透過回顧他們的歷史,揭示並解釋兩個彼此交纏在一起的文化遺產。一項是軍事工業研究文化的遺產,這種文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開始出現,並在冷戰期間達到高峰;另一項是美國反主流文化的遺產。自1960年代以來,學術界及一般人都以反主流文化人士最初的表達來描述反主流文化,即站在使冷戰國家及其軍事工業強大的科技與社會結構的對立面的文化。持這種觀點的人通常認為,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都是灰暗的年代,那是嚴格的社會規則官僚化的組織,以及美蘇經常性的核對峙的時代。而1960年代似乎是個人探索和政治抗議爆發的年代,其中大多數是為了推翻冷戰軍事工業的官僚體系。認同這一歷史版本的人認為,1968年那代人真實的革命理想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他們所反抗的力量的控制,並以此來解釋軍工聯合體的存留及公司資本主義和消費文化的不斷增長。
斯圖爾特·布蘭德,2020年
這樣的說法其實是有些道理的。儘管這已經深深寫入了那個年代的傳奇之中,但這個歷史版本忽略了一個事實,帶來核武和電腦的軍事工業研究的世界,也催生了自由的、跨產業的和極具創業精神的工作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及之後的研究實驗室中,在冷戰時期大量的軍事工程項目裡,科學家、士兵、技術人員,以及行政人員前所未有地打破了看不見的官僚壁壘,相互合作。他們接受了電腦及新興的控制論式的系統和資訊。他們開始把機構看成是一種有生命的有機體,把社會網絡看做資訊的網絡,同時把資訊的收集及詮釋看做理解技術、自然和人類社會的手段。
直到1960年代末,反主流文化運動的實質要素也是如此。例如,1967年至1970年,數以萬計的年輕人開始建立公社,其中許多人就建在山上和林子裡。布蘭德正是為這群年輕人創辦了第一期《全球概覽》。對於這些返土歸田的人,以及更多尚未建立新公社的人來說,傳統的推動社會變革的政治機制已經走到末路。同儕在創辦政黨和進行反越戰遊行時,他們(我稱之為新公社主義者)則選擇遠離政治,轉而擁抱技術和意識轉變,並將這些作為社會變革的主要來源。如果說主流的美國社會已經產生了一種衝突的文化:本土暴動與國外戰亂,那麼公社世界就是一片和諧。如果美國政府透過部署大規模武器系統來摧毀遙遠的敵人,那麼新公社主義者則會使用斧頭、鋤頭、擴音器、鎂光燈、投影儀,以及LSD 等小規模技術讓人們走到一起,並讓他們體會到共有的人性。最後,如果工業界和政府的官僚機構都要求人們成為專業卻心理分裂的人,那麼由技術引導的歸屬感體驗則會讓他們重新變得自立和完整。
對於反主流文化派別人士來說,美國研究文化的技術和知識成果具有強烈的吸引力。雖然嬉皮士們摒棄整個軍工複合體和催生出軍工複合體的政治過程,但是從曼哈頓到海特-阿什伯里區的嬉皮士都在閱讀諾伯特·維納、巴克敏斯特·富勒及馬歇爾‧麥克魯漢的著作。美國的年輕人透過這些人的文字,看到了一個控制論的世界:物質世界在這裡被看成了一個資訊系統。對於在強大的軍隊體系及核威脅環境之中長大的這代人來說,控制論裡把世界看成了一個統的、互聯的資訊系統的觀點,可以撫慰他們的心。在無形的資訊世界裡,許多人相信他們會看到全球和諧的希望。

由左至右,諾伯特·維納、巴克敏斯特·富勒及馬歇爾·麥克盧漢
對布蘭德及《全球概覽》後來的成員來說,控制論向他們展示了一套實現創業家想法的社會工具和話語工具。 1960年代初,布蘭德剛從史丹佛大學畢業不久,進入了舊金山和紐約的波希米亞藝術世界。當時他身邊的許多藝術家都被諾伯特·維納所寫的控制論深深感染。就像那些藝術家和維納一樣,布蘭德很快就成為了社會學家羅納德·布特(Ronald Burt) 所說的「聯網創業家」(network entrepreneur)。也就是說,他開始從一個知識領域跳到另一個知識領域,並在過程中將原先彼此獨立的知識和社會網絡連結起來。在《全球概覽》發行的年代,這些網路縱橫科研、嬉皮士、生態學,以及主流消費文化領域。而到了1990年代,美國國防部、美國國會、跨國企業(例如殼牌石油),以及各種電腦軟硬體製造商的代表也被納入其中。
布蘭德透過一系列的「網路化論壇」(network forum)將這些社群聚集在一起。他運用控制論的系統性言論,並藉鑒了研究領域和反主流文化領域的創業模式,創辦了一系列的會議、出版物和數位網絡,使得這些來自不同背景的人士相聚協作,並把自己視為同一社區的成員。而這些論壇又催生了新的社會網絡、新的文化類別及新的詞彙。 1968年,為幫助那些返土歸田的人更好地找到建造新社區所需的工具,布蘭德創辦了《全球概覽》。這些工具包括鹿皮夾克、圓頂建築,以及維納關於控制論的書,以及惠普最新的電腦。在隨後的幾期裡,除了這些裝備的討論,布蘭德還在田園嬉皮士的一手報告旁邊,刊登高科技研究人員的來信。這樣的做法使得公社成員有機會了解到,他們的抱負與美國主流社會的技術進步是相稱的,同時這也讓一線科研人員有機會看到,他們的二極管和繼電器能被公社成員喜愛,被用做改變個體和集體意識的工具。 《全球概覽》的作者和讀者使科技成為反主流文化的一股力量,即使在20世紀60年代的社會運動銷聲匿跡多年後,這股力量仍在影響公眾對電腦和其他機器的看法。
在1980年代和90年代,電腦越來越小,彼此連結更加緊密,企業也開始採取更靈活的生產方式。於是布蘭德和他的同事透過WELL、「全球商業網絡」(Global Business Network)、《連線》,以及一系列與三者相關的會議和組織,重新演繹了這個過程。每次都有一位連網創業家(通常就是布蘭德),把來自不同背景的人士聚集到同一個實體或文字空間。這些網絡的成員親手合作各類項目,並在合作過程中形成共同語言;有了共同語言之後,就會對計算機潛在的社會影響,對信息和信息技術在社會進程中的意義,對工作在網絡化的經濟秩序中的本質等議題達成共識;並且往往他們匯聚在一起所形成的網絡本身就應驗了這樣的共識。就算沒有如此,他們也會把從中得到的啟發帶回自身的社會和職業領域當中。因此,那些由《全球概覽》衍生的論壇的觀點就形成了一個核心櫃架,幫助公眾及專業人土理解資訊及資訊科技潛在的社會影響。慢慢地,這些網絡成員和論壇把微型計算機重新定義成“個人”計算機,把計算機網絡定義成“虛擬社區”,把賽博空間定義為“電子邊疆”(electronic frontier),一個如60年代末眾多公社社員所踏進的西部田園般的數位世界。
同時,透過同樣的社會過程,「全球網絡」成員也將自己變成了社會化和技術觀點的權威代言人,而這個願景恰由他們協力描繪而出。從傳統上來講社會學家以報紙和雜誌的職業標準來定義記者:記錄與自己無實際關聯的群體的輿論,若自己身處報道群體之中,則應置身事外地進行記錄。這種觀點認為,記者的聲譽取決於他發掘新資訊、對資訊進行可信的報道,以及將資訊揭露給公眾的能力(這裡的「公眾」本質上不同於消息來源群體和記者群體)。然而,布蘭德及「全球」系列刊物的其他作者和編輯們,卻是透過建立一個群體並報道這些群體的活動從而樹立起卓越的記者名聲,並贏得了許多獎項。其中《全球概覽》贏得了全美圖書獎(National Book Award),《連線》雜誌則獲得了全美期刊獎(National Magazine Award)。在「全球」所支持的網路論壇上,以及由此衍生的書和文章裡,科技領域的行家與政治、商業領袖會面,與當年的反主流文化人士交流。他們的對話使數位媒體成為了成員們所共有的獨特生活方式的象徵,以及個人公信力的證明。布蘭德、凱文·凱利、霍華德·萊茵戈德、約翰·佩里·巴羅等人,一次又一次地表達出在討論中湧現出的技術化社會觀點。
他們也被邀請到國會、大企業的董事會和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 1990年代中期,「全球網路」的成員遍及眾多主流媒體、商界和政府,連網創業家精神及其在經濟和社會上所取得的不證自明的成功,印證了那時許多人開始說的「新經濟」的變革力量。諸多政治家和專家認為,電腦和通訊技術融入國際經濟生活,以及企業大幅裁員和重組,都催生了新經濟時代的到來。如今人們不能依賴他們的雇主,他們必須自已成為創業家,要靈活地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去,從一個團隊到另一個團隊去,透過不斷地自學建立自己的知識基礎和技能係統。許多人認為,政府在這種新環境中的合理角色就是收手放權,不去監管正在引領變革的科技產業,以及科技產業所相關的商業。
這一觀點的支持者包括通訊領域的高階主管、科技股票分析師,以及右翼政治人物。凱文·凱利把他們都匯聚到了《連線》雜誌中。凱利曾是季刊《全球評論》(Whole Earth Review)的編輯,這本雜誌就是由《全球概覽》衍生而來。身為《連線》雜誌的執行主編,他認為整個世界是一串彼此緊扣的資訊系統,而這些系統都在摧毀工業化時代的官僚體系。對凱文凱利及《連線》雜誌的其他創辦人來說,一晚出現的網路似乎是新經濟時代的基石和象徵。他們認為,如果確實如此,那麼那些圍繞著網路生活及解除新興網路市場管制的人,可能就是文化變革的先驅。 《連線》雜誌刊載了許多關於WELL、「全球商業網絡及」、「電子前沿基金會」的成員的專題:這些成員交織在「全球網路」之中,同時《連線》裡也有關於微軟的比爾蓋茨,以及個人自由主義專家喬治吉爾德( George Gilder)的報道,甚至某期封面人物就是保守派共和黨議員紐特金里奇( Newt Gingrich )。
對於那些把20世紀60年代看做與傳統背離的人來說,當年的反主流文化運動者如今竟然和商界領袖、右翼政客走到一起,這根本就不可思議,也充滿了矛盾。但「全球網路」的歷史告訴我們,這一切都有可能。 19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運動者決定遠離政治,轉而投奔科技、意識及創業精神,將這些作為新社會的準則。他們當年的烏托邦夢想跟20世紀90年代共和黨的理想非常接近。雖然紐特·金里奇及他身邊的人對20世紀60年代反主流文化運動者的享樂主義嗤之以鼻,但他還是很認同他們對科技的崇拜,對創業的認同,以及對傳統政治的摒棄。隨著他們逐漸走進權力中心,越來越多的右翼政治家和創業領袖也開始希望能夠像布蘭德一樣獲得認同。
本書不是要講述反主流文化運動如何被資本、技術,以及國家所左右的故事。恰恰相反,我會講述反主流文化中的新公社主義者如何在早期就利用這些力量,且在隨後的時間裡,布蘭德及「全球網絡」繼續提供知識和實踐的環境,使得這兩個世界的成員彼此對話並認可對方的事業。但本書並非布蘭德的傳記。確實有必要給布蘭德寫個傳記,未來幾年肯定會有人去寫,但本書不會強調布蘭德個人的歷史,除非涉及他在重塑資訊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布蘭德在其他領域也有很重要的影響,特別是在生態學及建築設計方面,他自己的人生也非常精彩,但這些只能由其他人來記述了。我寫這本書的主要目的,是將布蘭德及其所創造的網絡對我們的電腦認知所造成的影響、對社會生活的關係所造成的影響,一一呈現給大家。在這個故事裡,布蘭德既是重要的參與者,也是新的科技和社會生活的主要推動者;其他「全球網路」裡的記者、諮商師及創業家也是如此。撰寫本書的挑戰就是要同時密切關註三個面向:布蘭德個人的才能、他所採用的連網策略,以及他所創造的那些網路越來越大的影響力。
於是我決定從四十年前大眾對電腦認知的改變歷程開始我的記述,並提到已被遺忘的那段冷戰研究文化與新公社主義者的反主流文化的密切關係。之後就以布蘭德為線索,首先介紹20世紀60年代的藝術圈,然後是西南地區的新公社運動,之後是20世紀70年代舊金山灣區計算機革命的幕後故事,最後是20世紀80年代及90年代的企業界。在這個過程中,我會穿插分析布蘭德所創建的網路和網路論壇的一些細節。讀者會發現,布蘭德對大眾的電腦認知所產生的影響不僅來自他發現社會和技術前沿變化的過人能力,還在於他組建起來的網絡的多元性和複雜性。最後我會總結布蘭德的創業策略,以及電腦、電腦通訊同反主流文化的平等社會理想的廣泛聯繫,這種聯繫已成為日益網絡化的生活工作、社會及文化權力結構的重要特徵。
雖然大眾傾向於認為這樣的模式是電腦科技革命的成果,但我認為,早在網路出現之前,甚至是在電腦進入尋常百姓家之前,變革就已經發生了。那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開始,也正是控制論及冷戰軍事研究的協作方式開始與反主流文化的公社主義社會願景相互碰撞的時候。